
琉璃版九龙九凤冠。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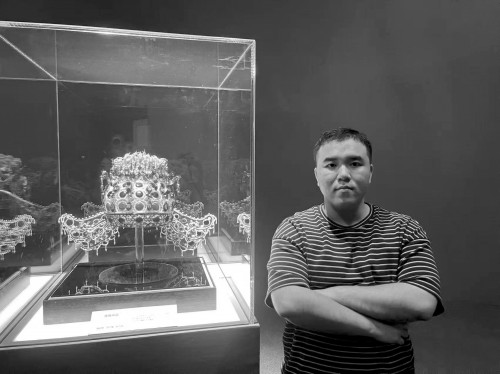
邹宇曦

孙启烨

陈玙强

甘宇宸
小时候,在福建老家青石巷的晨雾里,总飘着陶瓷窑炉的余温。对于1999年出生的邹宇曦来说,童年记忆里总有泥土在旋转的轮盘上渐渐隆起,最终成为能盛放月光的工艺品。这段记忆牵引着他报考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玻璃与陶瓷专业。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专业课上喷灯烈焰中流淌的玻璃液会彻底唤醒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将同三位热爱琉璃工艺的年轻人一起开设一家玻璃艺术工作室;更未曾预想,他们耗时两个月制作的琉璃版九龙九凤冠,会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向世界展示传承千年的琉璃非遗技艺。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传承
在流动的玻璃中对话文物
盛夏的上海像被倒扣的蒸笼,当工作室温度计指向42℃时,喷灯的火焰仍在吞吐着1300℃的热浪,邹宇曦戴着护目镜,脸颊上挂着汗珠,视线却牢牢锁在那根直径0.3毫米的玻璃丝上。这是琉璃工艺品的制作常态,邹宇曦告诉记者:“玻璃凉一分就硬,热一分就塌。手腕一抖,玻璃丝就会断。”
谈及那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九龙九凤冠复刻作品,自诩有些社恐的邹宇曦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介绍道,这件用古法琉璃复刻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由9条“金龙”、9条“金凤”、115块“红宝石”和4000余颗“珍珠”组成。看似由不同材质制成的凤冠,实则全由玻璃烧制而成。
让人惊讶的是,这件精美繁复的作品是由邹宇曦、陈玙强、甘宇宸、孙启烨四位年轻人共同打造。而团队的初衷也很简单,希望和几百年前的文物来一场隔空对话,邹宇曦说,“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匠人也能让琉璃在火焰里开出花”。
复刻九龙九凤冠的两个月里,工作室的墙面上总映着四个忙碌的身影。邹宇曦盯着火焰的眼神像在解数学题,专注于凤冠上“凤”的制作;陈玙强捏玻璃丝的手指稳如磐石,负责整体琉璃编织大框架;甘宇宸不断调试烧制琉璃的电流和电压,摸索凤冠上的“宝石”和“珍珠”的质感;孙启烨则对照自己的手绘图纸,潜心摸索凤冠上的“龙”。
淬炼
无数次尝试只为毫厘之差
在复刻九龙九凤冠过程中,即便衣服已经湿透,团队成员仍守在喷灯旁,紧盯着火焰中舞动的琉璃,藿香正气水成了他们最常备的饮品。邹宇曦回忆,“复刻九龙九凤冠时,最大的技术难题是细节塑型与固定,尤其是如何完美呈现龙鳞和凤凰羽毛的质感与形态,同时保证整体结构稳固”。
龙鳞和凤凰羽毛是凤冠上尤为复杂的部分,龙鳞需要用铁圈一点点压出来,凤凰羽毛则是用直径不到0.5毫米的玻璃丝逐步点画。这些细节不仅需要极高的手工技巧,还需要反复试验和调整,以确保形状和质感符合设计要求。
玻璃在高温下极易变形,比如龙鳞压形时稍冷就会收缩,需要把控好温度进行压形。一个晚上需要点扎50片,工作量巨大且容错率极低。“我们通过反复试验,逐渐掌握了玻璃丝的温度控制和操作技巧。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仔细分析原因,调整操作方法和温度参数,最终成功塑造出理想的龙鳞和凤凰羽毛。”邹宇曦说。
凤冠上的“珍珠”需要特殊电镀处理以呈现温润光泽,这个过程堪称“火与光的实验”。00后团队成员甘宇宸解释道,玻璃表面光滑,金属离子难以附着,需先用电解液处理表面,再逐步电镀,而电压和电流的控制至关重要,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效果。更具挑战性的是,团队此次复刻用的是几经周转淘来的60多年前的老式玻璃,烧制特性与常用玻璃不同。“我们逐档调整电压,从7.4伏到12伏,每次增加0.1伏,反复试验后才找到最佳参数,成功实现了珍珠的电镀效果。”
回响
国家博物馆展厅的温度
今年6月,淄博琉璃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邹宇曦代表团队去北京参加开幕式。展柜的玻璃映出那顶晶莹剔透的凤冠,也映出参观者的笑脸。它不再是冰冷的文物复刻品,而是一群年轻人用热爱焐热的时光结晶。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总有人愿意为0.3毫米的完美,“燃烧”两个月的光阴。看着在作品前驻足的观众,邹宇曦百感交集。他想起团队近40张的部件草稿,无数次调试的材料配比;想起凌晨3点工作室仍然亮起的灯光,初学技艺时被火烧掉的眉毛和手指烫起的水泡。
记者了解到,邹宇曦、陈玙强和甘宇宸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校友,班里只有他们还在坚持做琉璃。工作室名字“予燧”由陈玙强所起,暗藏深意,“我们三个名字里都有‘YU’的发音,所以用‘予’,取给予、奉献之意;‘燧’源自钻木取火的始祖燧人氏,既致敬创造火与技艺的先人、古老的手艺,也纪念我们在高温下挥汗如雨的青春”。
当问及为何坚持做琉璃,他们答案一致:因为热爱,在这份手工艺中能感受到快乐。“我和陈玙强是同一届的,通过学校老师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师弟甘宇宸。随后,经老师推荐,我们选择在松江大仓桥附近开了工作室。我们看好琉璃的发展潜力,上海有更多机遇,未来还打算和更多博物馆合作。”邹宇曦说。
忙碌间隙,邹宇曦常会和团队小伙伴走到仓桥下,望着悠悠古桥与盈盈小河,仿佛时光在此驻足——正如每一个醉心琉璃的年轻手艺人。琉璃是冷的,火焰是烫的,而支撑这群年轻人走下去的,是比火焰更炽热的坚守,是对琉璃手艺、对热爱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