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话剧《生之代价》在上海茉莉花剧场正式迎来首轮演出。首演结束后,该剧导演查文浩走上舞台,用极其温柔的语调呼应现场观众的感受:“希望这部淡淡的,有雨水,有雪花的故事,能够让大家体会到应该如何面对爱,面对孤独。”
在《生之代价》首轮演出间隙,这位90后导演做客青年报《上海文化Talk》栏目。什么才是“生之代价”?查文浩也在追问自己。他的答案谦逊,稍显保守,也有一反同龄人的清醒:在过分追求效率和回报性价比的时代,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应该思考如何排除效益和流量的诱惑,寻找“自洽”的路径,安心去做一个艺术的“匠人”。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戏里追问“生之代价”
青年报:话剧《生之代价》表达的内核是什么?
查文浩:《生之代价》这部戏的剧本太好了,很特别,它围绕两组城市中的边缘人物展开。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其中一组人物是残障人士,女性人设是一位40多岁的高位截瘫女性。男性人设虽然20多岁长相帅气,高学历,却从小患有小儿麻痹。根据剧情设计,需要安排两位残障人士来演。所以我们决定做这部戏时,第一点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演员。这个题材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特殊性,我们找到什么样的演员决定了这部戏的走向。我们很顺利找到了张佳鑫,可谓是“天选之人”,他是脱口秀语言类工作者,为这部戏带去了很多幽默属性以及他本人的特质。舞蹈家刘岩老师,在北京奥运会排练时受伤瘫痪,这几年依然在舞蹈领域的幕后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很适合她。我从这部戏里读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面对伤痛,如何在隔阂中获得理解,在劫难中追逐新生。
青年报:这个剧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
查文浩:读完剧本以后,我写下了这几句话: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每个人又如此渴望被理解,渴望被爱。排这部戏时,我一直在追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生之代价”?我相信走进剧场的观众也会同样去思考这个问题。走出剧场时,他们是否对于“生之代价”会有一些新的领悟。
就我的理解,它就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去付出爱,以及认为这份付出值不值当的性价比。现在,我们做很多事都会先权衡利弊,考虑做这件事值不值得,以期花费最小的努力得到最高的收益。大家都在考虑性价比和效率问题。其实,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错,我们当然应该提高效率,追求更大的价值,但是付出爱这件事,可能很难用性价比去做判断。在这部戏里,同样有此追问:当我们明知道付出情感,不会获得很高的效益,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付出呢?这一点,很打动我。
青年报:经常来上海演戏、排戏,如何评价这里的戏剧观众?
查文浩:这次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来上海工作,能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家们一起合作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上海整个的戏剧氛围,很多元,很丰富,很年轻,戏剧市场又特别好。每天,我能看到剧场外面有很多观众等候演员签名,等候拍照合影。他们看完戏,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写report,写得也特别专业,我对上海观众的印象是艺术审美特别高。他们对人物关系的理解、感受特别细腻,也很真实,甚至也加深了我对《生之代价》的理解。单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也许我们的理解是片面的,这些关于戏剧的讨论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创作氛围,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一部戏走到台前,并不是创作的结束,对于这台戏的生命轨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创作者和观众可以一起见证一部戏的成长,彼此也共同经历成长。
首先要拿作品说话
青年报:作为90后导演,也是互联网原住民,你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粉丝。如何看待流量,想成为“流量导演”吗?
查文浩:首先,有很多人关注你,有很多人鼓励你,是一件好事。但是导演更多时候是需要通过作品来跟大家交流。一个导演,一个幕后的工作者,总是站在幕前,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人交流?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吗?他跟大家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甭管是演员还是导演,都要拿作品说话。导演的很多工作,在剧组里承担的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过多去博取流量,未必是一件好事,它肯定是一把双刃剑。你是要代表一个团队、一个剧组的整体方向去面对关注的,以个人的身份去玩转流量,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也有人劝我可以多去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帮自己做宣传。但目前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扎实了。不论夸这部作品哪里出彩,是台前,还是幕后,或是舞美、音乐、服化、表现形式,这都跟我有关系,是一个团队共同创作的结果,它离不开任何一个创作者。
青年报:既是青年演员又是青年导演,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查文浩:我是演员,同时又是导演。做导演时,我觉得自己不能老是抛头露面;但其实作为演员,又需要增加一定的曝光度,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你要想清楚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观众。我觉得,走着看吧。观众不会以一个标签来认定你,包括全世界许多知名的演员,也同时担任着导演、编剧、制作人的角色。我们都是创作者,不论在哪个岗位,也都可以保持创作的热情。
需要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
青年报:你对自己的戏剧表达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吗?你想成为一个“多边形”导演吗?
查文浩:这得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你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是你作为导演的一个工作风格。在我看来,导演只是一个剧组的引导者,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家,也不是所有的舞台剧作品或者影视剧作品,它能称得上是艺术作品,真正够得上是“艺术”的作品也是很少的。可以说,很多导演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者,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组织者。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是有着多么高深思想的一个人。作为导演,需要具备不停学习,不停充实自己思想的积极态度。我很渴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艺术性的艺术家。
剧本如果很好,那是剧作家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作为二度创作的导演,需要通过很多种方式将它立体化、视听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品很好,这未必是导演的功劳,而是剧作家的功劳。从这一点上看,我的个人艺术风格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需要一直保持学习的过程。作为导演,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匠人”,需要具备匠人精神,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你得耐得住你手艺的培养过程,你要把基础打好,才能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手艺人。一个手艺人如何变成艺术家呢?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的,需要经历大量学习和思考;更需要大量实践,才能逐步找到并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
目前,我还处于摸索的过程中,因此还不想明确定义自己的艺术风格,否则路可能反而变窄了。比如说,这次的《生之代价》,它是一个清淡惆怅的生活流作品。它跟我之前的作品风格非常不一样。当时我还在想,为什么会选我呢?后来仔细一想,虽然这部作品大不同,但是我对它是有感受的。事实证明,这类题材我也能胜任。现阶段,我不太想为自己设定太多限制,固定一种风格。
青年报:你觉得90后导演的普遍特质是什么?你想成为传承者还是破局者?
查文浩:我觉得90后导演之所以凤毛麟角,是因为机会还是少。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作品,因此优秀,只是很多优秀的人,他还没有运气得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让我概括90后戏剧导演的特质,我不敢去定性。只能讲讲我自己吧。首先肯定不是一个破局者,没有人能破得了这个局。他一定是沿袭了前人优秀作品的思想精髓和内核前行,一定要沿袭这些文化脉络再去构建自己的表达体系,看待世界的方式。
先有守正,才能谈创新。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天才,他一定要看大量的中国经典作品,进行大量的思考,然后再去感受这个时代,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舞台作品,让观众找到共鸣。现在我的目标是,不管做哪类题材,都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品,不需要一种风格一以贯之,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独特的生命,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绽放出不同的个性色彩,这可能才是我的风格。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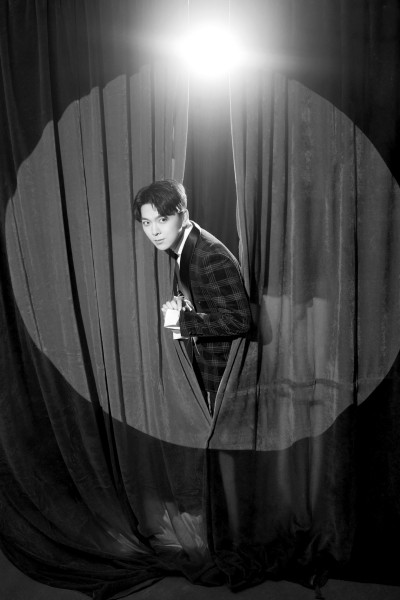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