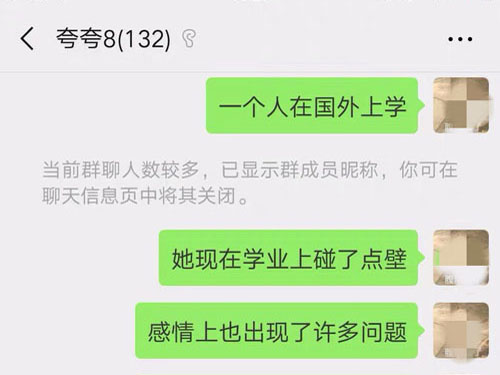80后热衷收藏老城厢界碑 建一个场,让上海摩登历久弥新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郭颖/文、图、摄 杨诚/剪辑
从前,上海人造房子,需要到管理机构申请,然后在房子占地面积的对角处竖起两块石头,以此为界进行编号,界碑由此而生。界碑的拥有者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公所、善堂、企业用地、私人宅所等等。有一位“80后”,专门到上海老城厢动迁的废墟中寻找界碑,以此留住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他叫陈败。
“我收藏的这些界碑都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这座城市。这些石头,是上海历史的亲历者,它们仿佛是有生命的,会诉说上海的过往。”
在陆家嘴的黄金地段,隐藏着一座400平方米的小型私人博物馆——上海有恒博物馆。
老上海的门牌、报纸、地图、熨斗、花露水……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陈,都是陈败的心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界碑。这些界碑上的字迹已经不那么清晰,但依然隽永,那是这座城市的记忆。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20年前来上海闯荡的‘新上海人’。”虽说是“80后”,但陈败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沧桑”一些。
陈败学的是美术专业,起初,他对于老上海的感觉就是:美。陈败称自己不是“收藏家”,而是一个“捡垃圾”的人。他捡回的,正是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
1999年,陈败来到上海。刚开始的三五年时间,完全是忙于生计,他当过报纸旅游版的美术编辑,给大企业办过杂志,即便是后来辞职下海开公司,做的也是上海大型文化场馆及艺术院团的剧目形象设计,干的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事儿。
十年前,上海迎来了城区“旧改”的高峰,随着原南市区老城厢一轮又一轮的拆迁,一些或埋在土里或被丢弃的界碑开始“浮出地面”。当时,陈败正好在拍摄与此有关的纪录片,他开始关注起这些神奇的石头。“那时拍了大量的影像资料,觉得这些界碑被扔了太可惜,索性费力收藏起来。”
陈败收藏的第一块界碑始于2011年,真正开始系统性收集是2013年,当时,整个十六铺地区集中拆迁,他就不分昼夜在废墟里“寻宝”。
“拆房子的人问我,你要这些破石头干吗?在我眼里它们可是宝贝。”当时,陈败一有空就去拆迁现场,不分昼夜地守在那里。然而,往往是去得早不如去得巧。“后来,我找了一个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的环卫工人,请他帮忙在有界碑的地方做个标注,这样一下子就找出很多界碑。”这些界碑后来挪到仓库里,光是分类就花了很长时间。
“界碑就是房屋建造的时候,放在墙角的两块石头,一般是斜对角,也有放在门前的。并不是所有的界碑都有收藏价值,我的价值在于集中性的收藏。”陈败笑言,他最关注的便是华界,也就是后来的南市老城厢。“那时界碑太多了,像堂界就有很多,不同人家的姓,就会有一个界碑。还有企业界,如上海市政厅界等。”陈败说。
事实上,这些年来,上海的文物部门也一直在极力保护界碑。但大量涉及民间善堂、同乡会所、同业公馆以及私人用地的石碑,或难觅踪迹或已损坏。
“我收藏的这些界碑都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这座城市。”陈败认真地说,不少人向他购买界碑,他说不卖,人家都觉得他傻。“收藏不就是为了卖高价吗?”可陈败不这么认为,他的每块界碑都在文物部门备过案,不能买卖。未来,他会把这些界碑都捐赠给国家。“这些石头,是上海历史的亲历者,它们仿佛是有生命的,会诉说上海的过往。”

陈败说这些界碑属于这座城市。
收藏界碑常常会有这样的遗憾,很可能昨天晚上看见的,今天再去看就没有了,因为拆迁,那些建筑一夜之间就会被夷为平地,界碑当然也就被当作建筑垃圾处理掉了。
陈败的博物馆名字叫“有恒”,这个名字来自于他错过的一块界碑。
“有恒洋行迄今所知进入上海最早的设计事务所,外白渡桥的设计方,几年前,我因为错过了一个电话,与这块界碑擦肩而过,这是我莫大的遗憾。”陈败告诉青年报记者,“有恒”这两个字的寓意十分美好,发音跟“有痕”相近,“时间是有痕迹的。”
“收藏界碑常常会有这样的遗憾,很可能昨天晚上看见的,今天再去看就没有了,因为拆迁,那些建筑一夜之间就会被夷为平地,界碑当然也就被当作建筑垃圾处理掉了。”陈败还错失过一块1942年的界碑,仅隔了一夜,第二天再去,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每每遇到这样的错过,陈败就会觉得很痛心。
陈败迄今已先后收藏了70多块界碑,展出的只是其中的20多块,原南市区界碑差不多有70%在他这里。陈败对这些千辛万苦收集来的宝贝也是如数家珍:“这块是‘同仁辅元堂界碑’,同仁辅元堂是近代上海最大的善堂,最初名叫同仁堂。”
据介绍,同仁堂正式成立于1804年(嘉庆九年),是由当时上海知县倡议,联合多家零散的善堂建立的半官方慈善机构,堂址就设在药王庙贴邻的乔家民宅,门前的一条小路就叫“同仁辅元堂弄”或“辅元堂弄”,这条路很短,只有三四十米,后来改为“药局弄95弄”。辅元堂由上海人梅益奎、海门人施湘帆、慈溪人韩再桥等发起创建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堂址与同仁堂为邻,向无力入葬的贫民提供棺木并建立义冢,1855年(咸丰五年)与同仁堂合并,合称“同仁辅元堂”。同仁辅元堂除了经营一段时期的慈善救济,又加上了挑除垃圾、稽查渡桥之事,实际上就是代理地方政府的部分市政管理。

陈败收藏的老上海物件。
“有一次,我乘飞机,带了一瓶老的花露水,安检时需要打开。瓶盖一打开,满屋飘香。”“我喜欢上海,因为是上海的文化滋养了我。”
有恒博物馆门口的“广告牌”颇有几分老上海月份牌的味道,上面写着“恒久记忆”4个大字。陈败坦言,除了界碑,他更喜欢老上海百姓家里用的老物件。
一个小小的日历机,已经锈迹斑斑,陈败却爱不释手:“你看,它的日期和月份都可以翻动。”电扇、打字机、风琴,都是年代久远的式样,虽然老旧,却有一种颇具年代感的低调奢华。
陈败不光收集物件,还收集“建筑物”,光楼梯扶手,就有多种造型,不同的形状和花纹,诉说着那个年代上海人的讲究。“黄陂南路860号”“开封路134号”的门牌号看似不起眼,上面的字却是从右往左排的,记录着它年代的久远。
墙上挂的一张“大阪朝日新闻社特撰”的《最新上海地图》最为“抢镜”,上面标注的每条路名都是中英双语的。“这是法租界,这是英租界,这是华界,就是后来的南市。”陈败说。
印刷品是最难保存的,可陈败还是收藏着老报纸,既有1932年一整年的《新闻报》全刊,也有两份单日的《申报》。“这是世界马戏大王来沪表演的广告,登了两次,一次是预告,一次是告别。”告别词是:今日表演压轴戏,何时重来杳无期。
老上海“四大公司”出售的日用品,也被陈败分列开来,其中还有“阿拉上海人”童年记忆中的“汤婆子”。“有一次,我乘飞机,带了一瓶老的花露水,安检时需要打开。瓶盖一打开,满屋飘香。”陈败的展陈里就有一瓶老上海的“明星花露水”。热水瓶、烟灰缸、饼干听、香烟盒……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段往事。陈败沉醉其中。
如今,有恒博物馆开张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有5000多人前来参观,只要通过微信预约,就可以前来免费参观。也有一些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不会预约,不请自来,陈败也接待。每当看到他们很高兴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年轻时用过的,陈败也会跟着高兴。撑起这个博物馆的开销不小,但陈败觉得这件事不能用经济来衡量。
陈败说促使自己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喜欢上海,因为是上海的文化滋养了我。”于是,便下定决心,守护好这份记忆。
“贯通古今之时空,讲好上海故事”,这是陈败追求的。“有恒是一个场,收藏城市生活之美,邀沪上人齐聚一堂;有恒更希望成为一座桥,提倡海派文脉的活态保存及新旧对话。上海摩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借着有恒,我们得以拓展城市对话空间的边界,为浦东文化助力的同时,更探索海派文化当下及未来的可能性。”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系:qnbxiaorenwu@sohu.com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郭颖/文、图、摄 杨诚/剪辑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