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我听见日子是锯木头的声音——从《银绳般的雪》看小说家卢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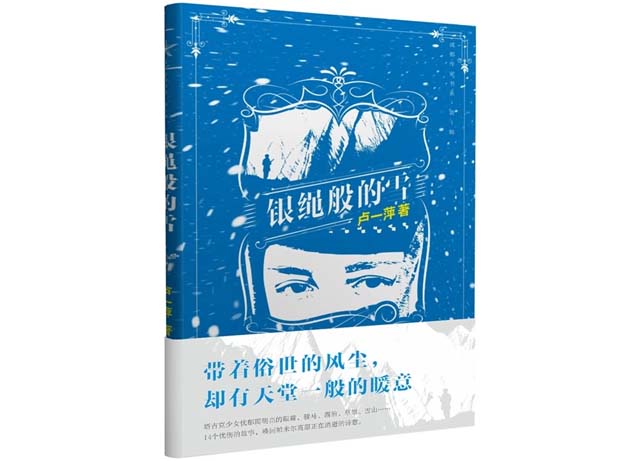
□马婷
小说家卢一萍无疑是为高原而生的,且他在这片雪域建立了自己的疆场,无论是散文集《走向高原》,还是小说集《银绳般的雪》,都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荒凉、神圣、苦寒却极富挑战与温情的世界。当我想要提笔写下只言片语因而再次翻阅这两本书的时候,书页上突然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双臂挽着抱于胸前,眼神刚毅而有柔情。这是我脑海中对卢一萍这个名字作出的唯一影像反映,可能因为,这样的形象于书刊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而我没有见过一个动态的他,以至于刻在脑海中的,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还有那样一个小书屋。有书、画、茶、香的小书屋。只能想象他在这个小书屋中读书、写作、喝茶的身影。
我强迫自己将思想再次集中在书本上,继续翻阅那些熟悉的文字,跟随他走向那久远年代,他记忆深处,我从未抵达之地。竟是因为对高原的向往结识一位作家,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圈,似乎应该先相识,再走入他的世界。我却是先走入他的世界,跟随他的文字,先了解了一颗翱翔的心,再去看这颗心包裹着的皮囊,一个刚柔并济的铁血柔情的勇士。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文字变得粗浅了起来。于是慢慢腾腾写下“翱翔高原的雄鹰”,写下“行走的勇士”,又犹犹豫豫地擦掉。那个时候他在我心中似笼罩光环,我那些平日里看着美好的词语,忽地就黯然失色了。我终于明白,即使我无限延续这些文字,也不足以形容他。他在书中说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是微小的,比他本身还要微小,他是将文字与他走过的崇高地域相比,但却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我知道他的身上其实是有许多标签的,我不用搜索也会知晓,诸如“雄鹰、血性、先锋”这样的词语。但我只想说我看到的。我即便没有见过一个动态的他,但透过《走向高原》和《银绳般的雪》捕捉过他的内心。于是撇开那些标签,我看到了他的豪迈与细腻,铁血与柔情,善良与澄澈。
他似乎总喜欢说自己飘然旷野,命如一萍,所以唤作一萍吗?我有时会思索,但又总觉直呼其名有些唐突。似乎只有“先生”与“您”那样的字眼,才适合我的年龄与文字路上后来者的身份。于是,我愿称他为先生。他是有古典英雄情结的人,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崇尚高贵气质和高贵气节的写作。而我与众多由古至今的女性一样,有最本初的英雄崇拜主义,这种英雄崇拜在当下社会,变成了对军人特殊的情愫。仿佛只要这两个字和那一身军装,就足以给一个人罩上一层光环,所以起初只是对他军人的履历的崇拜,就像人们所说的始于颜值,忠于人品般。当我接触继而沉溺到他那些行走、探索、深入高原的文章汇聚成的书本时,这种崇敬变成了对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的崇敬,也就是除却军人这层外衣后的他本身。原来光环之下,是如此有趣之心,又是那般随和。他本意文字便是交流,便是要寻找懂得,爱的。“懂”一个简单的字,却使世人寻而不得。所以对他,成了始于军人,忠于个性。
天地茫茫,却似乎愈是荒芜之地,愈能激起他上路的雄心。我虽然也憧憬远方,对那雪域高原无限神往,但这么久了,却唯唯诺诺,只让它们这些吸引着我的地方存在于期待之中而没有勇气迈出靠近它们的步伐。对,勇气,这也是坚韧又不容易的。他17岁从大巴山走出来时,便开始不断寻觅灵魂的故乡。而他书中的每一个地名对我来说,都是陌生又新奇的。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我都犹如闯入了一个新的领地。我在这个新的领地游弋、寻觅、惊叹、感慨、沉醉不知归路,久而久之,我的内心便绘制出一幅欲行走的地图,阿里、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喀什葛尔。这是大的地标,这大的地标下又是充满魅惑的每一寸土地。
他走过这每一寸土地,或步行,或骑马,甚至于骑牛历险,像一个浪子,以颓丧的态度来选择这种生存放逐的方式,继而与它们熟悉。与每一个达板,每一条河流,每一个牧民,每一头牦牛,每一只雄鹰,甚至每一根骨头熟悉。对,还有那一抹蓝。他还受到那蓝的蛊惑,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疆场,行走的疆场,写作的疆场。以荒原为背景,以高山、河流、牧民、战士为主角的,充满现实情怀的疆场。随后,他便在疆场内驰骋,犹入无人之地,并在此建造大厦,排兵布阵,找到技法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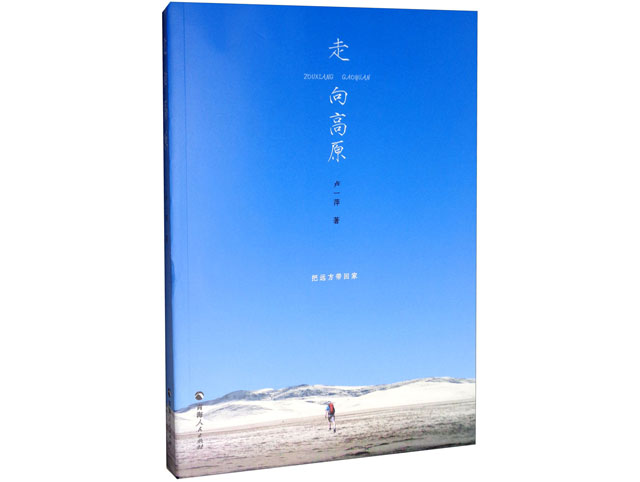
如今,我置身钢筋水泥包裹着的,坚硬冰冷的都市,却想要抬头看一看那蓝,是否如作家的眸子一般清澈。动辄6000米的海拔,《走向高原》让我看到了小说背后的作者,于是更能理解他的伟岸、他坚韧勇敢又纯洁的内心,如慕士塔格一般。他体内一切红尘之物皆被行走中的光透彻地洗涤净了。那些足迹可能被遗忘湮没,但文字不会。于是,札达、土林、古格王国遗址、象泉河、托林寺、咋达布热、塔什库尔干、慕士塔格、喀拉库勒湖、塔什库尔干石头、叶城、麻扎达坂、叶尔羌河、神仙湾边防连、界山达坂……伴随着《走向高原》这本书的翻阅,这些地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从未谋面的作家,我却跟随他走了那么多地方。他似乎一直在行走,而这行走始终离不开海拔、雪山、冰峰、河流、草原这些字眼。就那样长天为帐,大地为床,用脚和心走过漫漫长路,被高原上的风和停滞的时光洗浴。
他的心是洗涤过的、澄澈的。沐浴过阿里的阳光,经历过高原险阻的磨难,聆听过风中佛语的低吟,从而变得平静。所以才能在阿里背起去世的格桑老人就前行,所以才能在帕米尔高原,做《亡者的邻居》。我方明白有些人是注定要在高原上建立疆场的。因为他有胆识和魄力,善良亦无人能敌,连亡灵也要被感化。
我起先是被《走向高原》这本书吸引,被他征服高原的精神,被他细腻动人的文字,也被他无所畏惧的气概吸引。后来又先后读到了《天堂湾》《扶贫志》《银绳般的雪》这几本书,我终于敢说,我对这位先生是了解的了。而我是从小说集《银绳般的雪》中,寻到他那个疆场的。他的小说无疑跟他的行走,他的军旅生涯离不开。他在行走中看到世俗相,少数民族女孩的热情奔放、草原上的牧民、边防连的战士于是出现在了他的小说中。那些被赋予神性的鸟、越过山岗的羚羊、驰骋草原的战马、爱上哨卡小伙子的藏族姑娘、转场的塔吉克族女人,变成了他小说的素材。我边读边在旁边写下感想,恍惚间,眼前总会浮现一男子身影,在夕阳下,吹着风,平静地注视着远方,只有眼神,能看出柔情与坚毅。行走的作家有更深刻的感悟,对大自然,对军旅,对草原上的牧民,对各地的风情。
于是有了《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克克吐鲁克》《最高处的雪原》《孤哨》等诞生在他的疆场,收录在《银绳般的雪》这本书中的小说。这本小说集中无疑常出现那些熟悉的地名,它们是发生在塔什库尔干、帕米尔高原,塔合曼草原、慕士塔格雪山周边的故事。小说中常常出现莫合烟、雄鹰、奶茶、牛粪等字眼,又似乎总是围绕牧民或边防连的战士而展开。当然,我亦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草原上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看到了牧民的善良,生态坏境的变化和美好而纯真的爱情,这牧民抑或是战士的爱情,给冰冷的雪山增添了许多柔情和温度。而那匹叫“兴干”的退役军马,后来出现在了《克克吐鲁克》中,那对相互依靠着坐在塔合曼草原聆听马蹄声的老人亦变成了小说。我在一开始看这些小说的时候,觉得可能需要一张地图,因为我是那般浅薄和空白,那些地方,我仅靠着想象连不起来。但当我随着他的脚步游走了那么多地方之后,眼前便开始明朗了起来。
这明朗是对地理的,但感情却始终沉入其中。尤其读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银绳般的雪》中的《孤哨》一文时,许是因为它日记体的表现方式让我更易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与他融为一体。我开始为这个孤身一人守在天堂湾边防连六号哨卡多半年的陵五斗而焦急和心痛。焦急他何时才能离开六号卡哨回到连里,心痛他一人面对那漫长的荒凉孤寂与阴冷。一个独自守卫边防哨卡的哨长的日记,多么吸引人的小说形式。就是这一篇篇日记,让我直观地看到了主人公一步步的心理变化。从最初守这个哨卡时还能独自观赏群山、霞光、明月,觉得心旷神怡;到日子久了后逐渐涌上来的孤独;加之天气渐寒,高原的雪伴着狂风肆虐而来时心里更深的孤寂、阴冷荒凉之感,即便那时,他也依旧有坚守着不能放弃的责任。可当他得知自己守卫的哨卡已被宣布撤销,只是由于大雪封山连队不能接他回去时,那种依然守护却日渐加重的绝望,“这是多么苍白空洞的日子!我听见日子是那种用钝锯锯木头的声音”,“夜是这样的死寂,一切声音在此时都停止了。一切都死了,雪是裹尸布,裹着整个死去的世界”。他开始浑浑噩噩,失眠,生病,甚至于出现幻觉、失去信心而不知年月……直待最后得知六号哨卡依然恢复时,那一切坚守都有了意义,一切的孤寂、苦难都荡然无存,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警惕。当然他后来知道卡哨恢复只是为了让他活下去的谎言,他感激这谎言,但我也同时从这些心理变化中看到一个边防战士的责任心可以多么强大。
而收录其中的另一篇小说《夏巴孜归来》中善良的为守护草原而牺牲自我,甘愿搬迁到平原上开拓新生活的夏巴孜亦让人动容。小说出乎意料的结局,无疑让人心疼:善良的夏巴孜离开塔合曼草原,只成就了同学由乡长变成副县长,而他却成了傻的代名词。其中又似乎暗含了地域之外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文中他们到了平原后醉氧的那一段描述又让人觉得幽默风趣,加之结尾的处理,仿佛带有某种喜剧色彩。这种幽默风趣,我在读书中另一文《北京吉普》中,人们猜测我被关起来的原因是我用马鞭抽破了县长滚圆的大肚皮,县长肚子里的肥油淌了一地,以及传言我用套马杆套住并拉翻县长儿子的吉普那一段时,亦有感受。此外,书中《最高处的雪原》和《孤哨》等小说中对风雪侵袭下恶劣的高原环境的描述,不仅将他的文字功底淋漓尽显,更是增加了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
那些作品末尾留着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亦会让我恍惚。这个连天界都征服了的男人,在自己的疆场内开始得心应手地构建各种故事,这些故事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许他早就将高原当成了战场。这些年,整个西部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内心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文字上的小王国。走在路上对他而言已是生命的形式,正如他所说的,身上以前是农民的乡土味,之后是大兵味,然后是帕米尔高原的牧场味。这种牧场味,无疑,已根植进内心。但正是因着这牧场味,我才嗅到了那草原上驰骋的汉子的铁血与柔情,刚毅与纯真混合着的勇士的气息。
卢一萍:《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天堂湾》《帕米尔情歌》,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贫志》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等。马婷:1990年生于陕西扶风,著有散文集《十亩之间》,散文合集《忆梦昔年》。曾获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全国青年散文大赛银奖、陕西青年文学之星荣誉称号、《延河》杂志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等。
马婷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