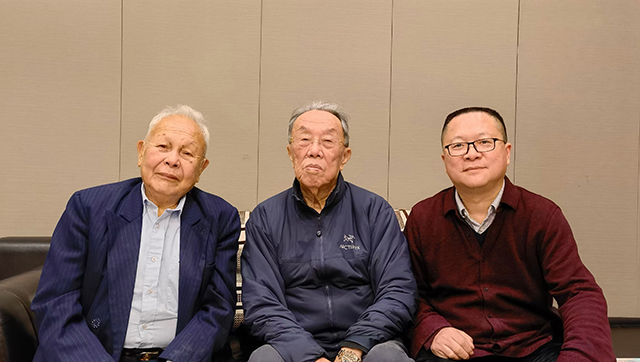写在淀山湖畔的“博士论文”

依湖而建的原野学社是徐驰参与乡村振兴的一次实践。本文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近日,不少与乡村规划、乡村振兴相关的论坛沙龙直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除了内容精彩,很多看直播的观众都被会场环境惊艳到了。专家们坐而论道,身后是一片田野风光,一个个学术活动,办出了情景交融的文艺色彩。
这个空间,是善湾村原野学社驻村规划师、主理人徐驰在淀山湖畔打造的乡村文化产业基地。作为一名从同济大学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徐驰尝试着结合理论研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江南钟灵毓秀的乡村土地上续写一篇“博士论文”。

徐驰
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
兴野文化创始人
善湾村原野学社驻村规划师、主理人
已完成的第一章
从前端向后端的转化
徐驰出生在农村,同济大学本科毕业,他拜入中国建筑界泰斗童寯先生的后人童明老师门下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了规划设计的“国家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不到一年,就开始独立负责项目。
按照肉眼可见的轨迹,徐驰的未来职业生涯大概率是这样的:成为部门负责人、评上高级职称,经常以专家身份出席各种论坛和项目评审会,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忙得没有双休日……
但是,在徐驰参加工作第四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离”。他生了一次病,动了一个小手术,这让他有了难得的安静思考的机会。回顾四年的工作,他突然觉得,原本看起来充实无比的工作中,却鲜有能称得上“作品”的存在。他很形象地举例说,作为规划师,在某个历史保护建筑外画了一道线,让它有了被保护的规划依据,“但这道线能称得上是作品吗?”在这四年里,徐驰虽然参与了很多大项目的规划和论证,但因为种种原因,很多项目方案最后成为了决策咨询的参考。青年学子对事业和成就的追求这一刻开始跃跃欲试。
身处中国规划设计的前沿,他也开始感受到了行业发展的变化。随着大拆大建设逐步被越发精细化的城市建设取代,建筑规划行业也隐隐触碰到了“天花板”。
躺在病床上,他做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辞职、读博。
这样的选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巨大的阻力。对于儿子要放弃这么一个“金饭碗”,父母的担心和反对接踵而至。但是,看似文质彬彬的徐驰却格外坚定,他回到了曾经求学八年的同济大学,开始了他职业追求的下半场。
虽然博士读的还是本专业,但已经有了四年实践经验的徐驰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了建筑规划行业的变化。他与室友成立了一个公司,却不以他们熟悉的规划领域作为业务方向。徐驰说,随着房地产行业“见顶”、存量物业不断累积,规划设计也应该顺应潮流,由前端的空间规划、建筑设计向后端内容策划和运营管理转化。
在规划设计业务收窄的今天,徐驰的转型还是在田野中见到了成效,长三角地区一些重要的规划设计运营全过程项目开始找上门来了。

孩子在营地里玩耍。
刚写好的第二章
从沙龙向实战的延伸
为了做好“后端”,徐驰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中国文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徐驰认为,读书是学习,跟各行各业的人交流也是学习。作为专业规划师,他总觉得自己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自己的知识还不够多,他开始举办和参与各种内容的沙龙。
他在武康大楼的画廊办过沙龙,在徐汇滨江的群岛咖啡办过沙龙,徐驰看着各行各业的精英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在不断汲取知识的同时,每一次见闻和交流都让他更加感到自己的不足。
在沙龙讨论中徐驰渐渐地发现,在这个“存量时代”里,曾经一招鲜吃遍天的老套路已经难以跟上新形势,某些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在城市空间的营造方面开始失效,而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广袤的天地中,大量乡村空间更需要有规划背景的“主理人”去耕耘和实践。
此时,他觉得“条件似乎成熟了”,乡村会给他机会,让他将曾经留在纸面上的策划落地,通过实战检验自己的知识、观点和能力。在师兄的牵头下,他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善湾村,在湖边一块废弃的宅基地上,以乡村规划师的身份开始了他作为乡村文化产业主理人的尝试。徐驰的“博士论文”在这里进入了正题。
徐驰认为,“社会也是一个科研的课堂”,特别是对于规划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来说。当徐驰走出办公室、走进农村时,便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科研路,“去研究规划怎么落地,我认为也是科研。”徐驰说。正所谓“一念起后天地宽”,这个选择让徐驰感觉到视野打开了,从学院派走向实操。
房子建起来了,他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开民宿,尽管周边有相当成功的民宿作为现成的样板。他把这个地方定位为新型的研学基地。就在这栋建在田边湖畔的漂亮建筑里,徐驰跟记者分享了他的“发现”:你知道,在高楼大厦的办公楼里开会和在湖畔田野开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人们大脑的开放度是不一样的,通常在没有束缚的环境下,发散性思维会更强。
于是,淀山湖畔就有了这么一座让人惊艳的文化沙龙场所。房子正前方就是秀美的淀山湖,他又设计了一家严选书店,请各行各业的“大佬”推荐书籍,游客们可以坐在湖边的蒲团上,喝着咖啡翻着书,听着讲座聊着天。
徐驰和他的伙伴将这个基地命名为“原野学社”,理想中,这里可以研野学,兴野趣,品野食。在这里,有观念的碰撞,有乡野的鲜甜,有帐篷可以野营,有农田可以观察。一个全新的业态正在淀山湖畔孕育成形。

原本荒废的草坪变成了露营的好去处。
正在写的第三章
从“事儿”向事业的努力
“博士论文”写到这里,徐驰却不满足,他自认为现在所做的还只能叫做“事儿”,要把“事儿”做成“事业”,有待于进一步学习和实践。
虽然出身农村,也很喜欢农村的环境,但是初来善湾村,徐驰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白”。为了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他找当地的老农聊天,一找便找了10位。现在他知道了,在这里种稻子,一亩两亩没法当产业,必亏无疑,只有种植面积达到百亩以上,农民才会有稳定的盈利;他也知道了,开民宿不光是造一幢房子、请几个工作人员,也需要依靠当地的产业生态,莫干山的民宿开得红火,换一个地方未必如此。
为了跟当地村民打成一片,他那间漂亮的会议室每年都会留出60场,为村民免费放电影,还会举办农业科技培训讲座。这里的咖啡价位不高,附近小区的居民常常过来捧一杯咖啡欣赏湖景。
基地旁的废弃草地被利用了起来,徐驰搭建了几个大帐篷,满足露营一族的需求。
有团队来这里团建,做完培训,在湖边烧烤,风景秀色可餐;有研讨会在这里举行,金句与稻香齐飞,思想共波涛起舞;有家长带小孩露营,白天识稻谷,晚上看星星……
后来,徐驰也准备做民宿,但他想把文化和研学做透了,才将民宿作为基地的配套。通过调研,他知道了,农村需要的不仅仅是将老房子改造漂亮,没有内涵、没有文化、没有产业,再漂亮的村子注定是空心的。
因此,他把精力放在文化沙龙和高校研学上,提高文化活动的层次和规格,扩大高校圈的影响。他说,原野学社最有价值的不是建筑,而是跨界的理念。规划师做后端运营是行业的跨界;水乡村野举行学术研讨是场域的跨界;选择吴江善湾村,地处长三角两区一县的交界处,那就是长三角区域的跨界。通过跨界形成的产业生态,一旦做大,就会对善湾村的产业导入和培育形成示范效应。那时,也许他会借更多的场地扩大经营,也许会有更多的人介入这一行业形成产业集聚。到那时候,这篇“博士论文”才算真正收笔。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