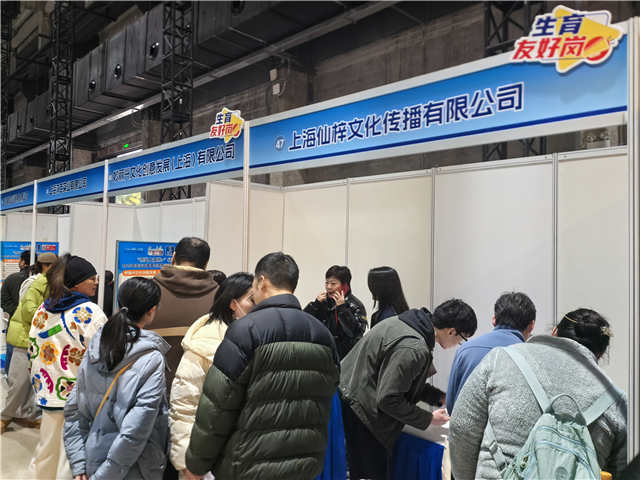《百年孤独》的雨落在墨西哥街头,一位插画师的跨洋文化寻踪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
自由插画师郭文媛一边讲述着结束于今年春节前的84天墨西哥之行,一边将被颜料渗透后厚到几乎快要合不上的速写本拆开,近80页插画赫然堆叠在桌面。倒也没有把画当成故事线索,只在一些记忆前翻出来用以“佐证”。从人物画像上的项链来历讲到该人物的国家认同;从当地新结识的外国友人在唐人街习得的中国生活方式,聊到上世纪40年代跟随丈夫所在的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来到上海的马丁太太……她一次次拍着脑袋喊“是不是扯远了”,其实这样反而离那片土地更近了。
热门剧集《百年孤独》第一季播放期间,郭文媛正在墨西哥狂欢,墨西哥正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写下《百年孤独》的地方。大学毕业的这些年里,她一次次带着高中读原著所残存的记忆前往拉丁美洲,在哥伦比亚的香蕉林里干活,摘香蕉再去偏僻丛林投喂猴子,这让她想起书里的香蕉公司;在厄瓜多尔西海岸的亚马孙雨林里被蚂蚁疯咬,这让她想起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啃噬……而这一次,确切来说是讲完故事后,她惊觉她的墨西哥朋友大卫像极了奥雷里亚诺上校,意料之中地因为他的孤独。

在哥伦比亚南部的雨林地区做志愿者期间,郭文媛画下了被蚂蚁噬咬时仿佛浑身火烧的瞬间。
孤独由来已久
重逢“奥雷里亚诺上校”
郭文媛站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民宿门口的石墩上,焦急地眺望四周,等着大卫开车来接她,上一次见面还是八年前,她不确定现在两人会不会变得生疏,以至于要保持礼貌的距离。“他给我留言的英文单词说的是一辆货车,我脑海里任由刻板印象开始天马行空起来:这个27岁的墨西哥人现在不会成为毒枭了吧?货车是用来拉一些见不得人的货吧?”思绪还在紧张地翻飞,一个脑袋从车窗探出来,熟悉的声线瞬间把郭文媛拽回现实。其实只是一辆普通的轿车,大卫除了略有后移的发际线,所有感觉一如从前。
一边与大卫聊天,一边执起画笔,郭文媛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位老友的细节,但画面上的大卫头发比实际浓密不少,头顶还环绕了一圈节庆头饰。回到上海后,她给很多朋友看过这趟墨西哥之行的画作,他们不约而同最喜爱大卫这一幅,“或许是深厚的友谊让我画得更有感情。”现场的大卫更是泪眼婆娑地看着她,“你现在竟然真的成为了一名艺术家!”2017年,郭文媛和大卫在中东地区做了一年志愿者。闲暇时分,郭文媛用丙烯颜料刷着露天区域的桌椅,甚至是自行车车座和车架,当时大家似乎都没有理会这样的即兴行为,权当是疯狂的消遣。

郭文媛在中东当志愿者时改造自行车。
“时隔近十年,终于在大卫的老家再次相遇,我们曾经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从零开始,在内盖夫沙漠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像两个士兵,两个初生牛犊,无关性别、国籍、年龄、语言……”这是郭文媛的文字记录,她将大卫因沉湎回忆而盈眶的热泪比作加利利湖的湖水。而这么多年来,大卫几乎没有长距离地离家,也没有再见过加利利湖,“他从来没有融入过这里,但他很明显融入了上层生活。”
郭文媛解释,大卫的爷爷是波兰犹太人,他带着妻子移民了墨西哥,生下了大卫的父亲,而大卫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以前大卫去以色列做志愿者正是父亲去世后的散心。父母很早就在墨西哥定居,大卫的国籍便成为了墨西哥,又由于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习惯性将自己封闭在精致的小世界里,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一定距离,甚至对全民狂欢的亡灵节也提不起半点兴趣。比如墨西哥法律规定不准在公共场合喝酒,借助一年一度的亡灵节,大家却得以端着酒瓶在街道上干杯痛饮,更以此宣泄一番平日被俗事缠身的压力,但这对大卫来说,没有半点吸引力。
奥雷里亚诺上校厌倦战争后回到马孔多,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终日反复熔铸小金鱼,做好了就化掉,化掉了再接着做……这一条条从童年游来的小金鱼占据了他的一生,鱼贯而入的却是始终无法摆脱的孤独。“我想去参军。”大卫认真地说,不过这只是将心里话抛向信任的朋友,并不需要等待任何反应,因为他深知母亲会阻止。

郭文媛时隔八年与大卫在墨西哥重逢。
死亡不是终点
亡灵节感受人生百年
当得知郭文媛如今多了一个名字——Rosa后,大卫吃惊地问,“你怎么会叫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墨西哥名字,而且非常过时,属于上一代的墨西哥老太太才会取的名字。”前些年,当意识到自己要专业从事插画创作时,她立马给自己取了一个符合艺术工作的花名——Rosa,正好是西语拼写。在另一张送给大卫的画像上,她认真地署上对方熟稔的名字——Guoguo,在大卫这里,是不是一名艺术家无关痛痒。
听到大卫的解释后,她反而灵光乍现地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这位有着一张东方脸庞的姑娘Rosa,变成身穿白色大花连衣裙、头顶盘了一圈麻花辫的矮个墨西哥老太太Rosa。连衣裙上的花朵是墨西哥常见元素——万寿菊,到了亡灵节前后,万寿菊如同一颗颗耀眼的太阳,四处抛洒温暖,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暖意来自对人生的积极体悟。

“亡灵节的意义在于彻底抹除了人们对于死亡的刻板印象,死亡并不是肉体的死亡,当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忘记你,才是真正的死亡。”郭文媛从2020年开始大规模的系列插画创作,一直保持着高产状态,“当我一再意识到生命难免有意外,就想尽可能多记录,在世界上留下一些自己活过的痕迹。”2022年,她在上海南昌路的一个社区公共艺术空间举办了第一个展览,记者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这位让人如沐春风的女孩,因为每次一见面就能感受到其无穷的生命力。此次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各大平台举办过了自己的画展。
在墨西哥的第一周,郭文媛几乎没有时间打开这个速写本,“我根本舍不得睡觉,只想抓住机会跟人喝酒聊天,因为只要拿起画笔就会耽误很多时间。”正处亡灵节的前一周,街头巷尾就已经潮涌着狂欢游行的队伍,每分每秒似乎都在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这种由兴奋裹挟的窒息感却令人身心愉悦。戴着夸张的墨西哥玉米帽子的街头乐队演奏着,烟火跟随舞蹈跳动,龙舌兰在教堂门前疯狂生长,公共墓地被新鲜的万寿菊和绚烂的骷髅头装饰淹没……24小时不停歇的游行和音乐会,让人几乎不用睡觉。

墨西哥年轻人的读诗会。
后来的日子她才平静下来,开始有一些空余时间用来画画。每年11月1日和2日是墨西哥亡灵节,这是一场纪念逝者的大型活动,而2024年11月3日是郭文媛的30岁生日,她在几年前就盘算着一定要赶在这一天前抵达墨西哥,正好衔接着庆祝自己的生日,预演一出向死而生的壮烈感。实际上她在去年10月25日就提前落地墨西哥城,这些感受如今早已成为她画笔下流动的记忆。
“跟着树冠走,跟着人流走,跟着大街小巷不断冒出来的亡灵节圣坛走,跳蚤市场的老头、街边玉米饼推车、卖热巧克力的老太婆、美容店小妹、古董店兼职的美院学生,每个人都给我留下一条或几条重要线索。”一个夜晚,郭文媛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小型画廊开幕式和读诗会,最终被拱上台挥舞着双臂用中文念了一首2019年写于哥伦比亚亚马孙雨林的打油诗,不禁窃喜,“这群迷人的墨西哥年轻人,怎么这么快就和我成为朋友了。”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