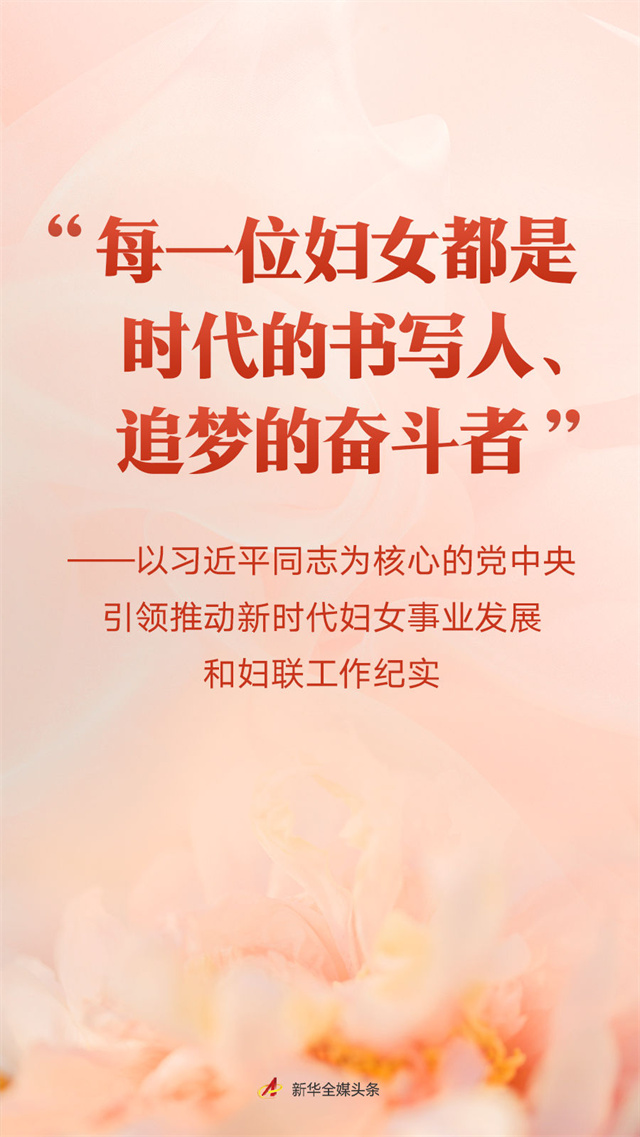史学“福尔摩斯”,复活历史现场

历史的谜团等待今人探索。图为游客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新华社 图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荆轲刺秦王是《史记》的经典篇章,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两千多年来,这个裹挟着悲壮与传奇的故事被反复讲述、演绎,似乎所有解读角度都已穷尽,难再有突破。
但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于习以为常的史料细节里洞察到缝隙,进而揭示出被遮蔽的历史图景。李开元教授的新作《刺秦》便是如此。他以“历史的福尔摩斯”之姿,通过细读《史记》文本,结合考古发现与合理推想,揭示刺秦事件中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带领读者穿越迷雾,走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感受历史研究的魅力与深度。
隐秘的目击者
青年报:读《刺秦》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史记》里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描述竟然来自一个被忽视的小人物——夏无且,就是那个把药箱扔向荆轲,救了秦始皇一命的秦国医生。是他留下口述,然后口口相传,最终传到司马迁那里,成为他描写刺秦的主要素材。您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
李开元:这个过程比较曲折。我们知道,《史记》里有三个篇章最为精彩,就是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项羽乌江自刎。它们的文字非常优美,戏剧性很强,富有动感。所以长期以来被怀疑不是史学,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因为司马迁没有在现场,没经历过,怎么能写得那样活灵活现?一定是虚构的。但我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三个篇章都由当事人讲述,其实是口述史。项羽乌江自刎是司马迁根据他女婿家传下来的口述写的,鸿门宴是依据樊哙的口述写的,而荆轲刺秦王,就出自夏无且的口述。
在《史记》里,夏无且这个人其实在两个地方出现过。第一次是在荆轲刺秦的现场,他拿药箱去砸荆轲,没砸中,但分散了荆轲的注意力,为秦始皇创造了反击的机会。事后秦始皇赏赐了夏无且。第二次出现在《刺客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感慨说:世间流传荆轲把秦王刺伤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当时在场的医生夏无且曾经告诉公孙季功和董生,说没这回事,他俩又讲给我父亲司马谈听。这就给了我们合理推想的空间:夏医生一直活到西汉初年,他把刺秦的故事讲给公孙季功和董生听,他们又讲给司马谈听,司马谈记录下来,或者讲给司马迁。这样就把荆轲刺秦的流传脉络捋清楚了。
青年报:除了这样的推想,还能从文本中找到证据吗?
李开元:其实你重新去读荆轲刺秦王,就会发现处处是医生的眼光。里面说荆轲左手抓住秦始皇的袖子,右手一刀刺过去,没刺中,秦始皇拔出剑,一口气向荆轲砍了八下。数字特别精确,八下,司马迁在别的地方都没写得那么精确。那很有可能就是夏无且说的,因为他是医生,要验伤,所以知道。这样,我基本可以确定荆轲刺秦王这篇源自夏无且的口述,所以才那么生动,而且很真实,绝对不是司马迁天马行空虚构的。

司马迁像。
刺秦现场意外的转折
青年报:您还有一个颠覆常识的说法:原本刺杀秦始皇的任务不是荆轲自己执行的,而是交给他的助手秦舞阳,但秦舞阳临场慌乱,荆轲不得不亲自动手。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李开元:通过细读文本。《史记》描写荆轲觐见秦始皇的原文是:“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注意,荆轲手捧装有秦始皇仇人樊於期人头的盒子,秦舞阳拿着的才是地图。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初刺杀秦始皇的任务应该由秦舞阳执行,因为匕首在地图的卷轴里。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秦舞阳心理素质不行,一上场就惊慌失措了,走不动了。但荆轲的心理素质非常强,他笑了,对秦始皇说,秦舞阳是“蛮夷之鄙人”,没见过大场面,吓坏了。最近考古队在秦咸阳城遗址挖出了六号宫殿,被认为就是荆轲他们来到的那座宫殿,极其宏大,初来乍到确实很容易被震慑住。秦始皇就说:荆轲,你把地图拿上来。于是因为局势的变化,荆轲只能自己拿着地图走上去,在秦王面前打开。
青年报:这样说来刺杀失败情有可原,原计划被打乱了。
李开元:是的。本来安排秦舞阳行刺,就是因为他剑术高明,“年十二,杀人,人不敢忤视”,他十二岁就杀人,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可见气场之强大。但刺秦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秦舞阳到了现场就脸色变白,话说不出来,路也走不动,根本无法执行。荆轲的剑术就不是很高明了,行刺失败,也不意外。刺秦的消息传出后,跟荆轲打过交道的鲁国游侠句践感叹:可惜了,荆轲对剑术不是很精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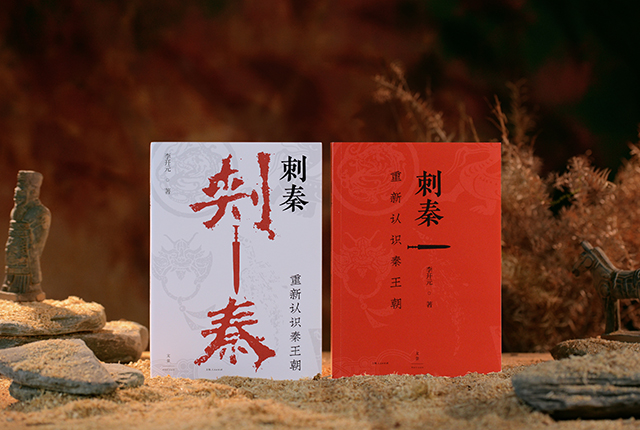
李开元新作《刺秦》。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刺秦失败还跟荆轲的犹豫有关,不过这个也很具颠覆性,因为您认为荆轲本来并不想杀死秦始皇,而是逼他就范,签订条约?
李开元:这是荆轲自己说的。刺杀失败后他背靠铜柱,笑骂道:“之所以没能成功,是想生擒秦王,迫使他签订誓约书以报效燕太子丹。”再往前看,其实燕太子丹一开始的图谋就是劫持秦王,迫使他归还侵吞诸侯的土地。如果秦始皇不同意,再杀掉不迟。我认为荆轲是按照这个预案执行的,所以先抓住秦王的衣袖,用剑锋威胁他。但是分寸不好拿捏,被秦王瞅准机会挣脱了。
青年报:刺秦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秦始皇的剑太长了,情急之下拔不出来,群臣在殿下大喊“王负剑”,秦始皇才拔出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负剑”历来被解释为“把剑背在背上,拔出来”,但您推翻了这个说法。
李开元:其实是影视界的朋友提醒了我。我跟导演陆川是朋友,有一次他问我:秦王的剑为什么要背在背上才能拔出来?我们做过场景还原,无论如何拔不出啊。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遇到了相同问题,他想了个办法:秦始皇配着剑跑,经过太监身旁,太监一把拉出剑鞘,剑就出来了。后来我在日本演讲,来了一位铸剑师,他背了把一米多长的剑,左手握住剑鞘、右手握住剑柄,往下一拉,剑就出来了。他说这是日本的武藏流剑法。我非常高兴,但也有一个疑问:中国的剑术跟日本的不一样,秦始皇会这样拔吗?
有一次,我遇到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他前两年已经去世了。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就提出了关于“王负剑”的疑惑。没想到孙机先生早就研究过,而且写过论文,专门讲中国古人是怎么佩剑的。原来战国时流行一种方法,长剑的剑柄上有一个扣,可以扣到斜挎在胸前的一根肩带上,打开扣,剑就可以移动。所以“王负剑”不是把剑背到背上,而是顺着肩带往后推,顺势拔出。
青年报:我觉得您的研究非常细致,善于从细节入手,层层推进,接近真相。
李开元:这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就拿《史记》里的口语成分来说,其实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我,而是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他敏锐地注意到荆轲刺秦王里三次出现“时惶急”,就是太急了,这是秦汉时的口语。宫崎市定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荆轲刺秦王、鸿门宴还有项羽乌江自刎,为什么写得那样活灵活现?这是司马迁去看戏,演员们正在演绎这些故事,司马迁一边看,一边记录,甚至把当初的一些口语,包括人物的动作也记了下来,然后用文字复原出来。
我刚开始看到这种说法惊为天人,后来见识更深了,觉得不对呀,中国戏剧要到宋代才大发展,而宫崎市定把宋代的勾栏瓦舍放到了汉代,那我就要打个问号了。但他发现《史记》里的口语遗留,是很了不起的,对后世学者很有启发。我就是从这里入手,重新解读荆轲刺秦王的。

《史记》确立了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核心范式。
在考证和叙事之间
青年报:通过您的讲述可以看到,研究历史还需要推理和想象。
李开元:研究古代历史和研究近现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材料繁多,而古代历史存在大量空白,需要想象力和推理能力。我呢,打小擅长数学,喜爱推理,是一个科学控,自认在这方面有一点优势,所以这些年我热衷于扮演“历史的福尔摩斯”,邀请读者针对一些历史之谜,做一番侦探破案的尝试。
青年报:其实您从前不是这个路数。2000年出版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非常学术,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但之后您好像“失踪”了,再出手就是《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一直到最新的《刺秦》,不再是论文模样了,叙事流畅生动,充满想象力。
李开元:其实中国历史学向来有注重叙事的传统啊,司马迁就是杰出代表。只不过近代以来,大学历史系只注重写论文,忽视了叙事,在学科评价体系中叙事不被重视。试想,司马迁进入现在的历史系,《史记》可能只会被当作资料汇编,因为它不是论文,不符合学术规范,不在学科评价范围之内。
我们抛弃了历史叙事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只搞研究,把历史学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只探讨一些非常高深的东西,这确实有利于彻底解决某一个问题。但历史学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事情却消失了,史书被完全当作资料。更严重的是,历史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写历史的人,那以后谁来写历史?所以我一直强调,研究与叙事并重。当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和史学大家邓广铭先生多有交往,邓先生治学就是研究与叙事并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现在要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青年报:但有人认为,历史不能讲得太好看,否则有“失真”之嫌。您怎么看?
李开元:我认为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也要求美,叙事之美。两者并不矛盾,是可以平衡的。叙事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这与艺术是相通的。艺术家追求风格的转换,如果一辈子只会画一种东西,那这辈子就白活了。我们做学问的人,一辈子用同样的文体写同样的问题,却自得其乐,不是很可悲吗?
青年报:您想恢复的另一个传统是行走吧?读您的书,感到您去过笔下每一处历史现场。
李开元:这也是司马迁的传统。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二十岁时“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从足迹来看,从南到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史官后,司马迁去过刘邦的故乡拜访遗老,去过韩信的故乡,打探他年轻时的轶事,包括荆轲刺秦王等篇章,也采自当事人的口述。司马迁开创了行走的传统,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宋代司马光,还有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垣等人,都强调行走与读书应并重。
青年报:最后我们回到《史记》,您的几本书其实都是围绕《史记》展开的,解答里面各种各样的谜团。那么在您心中,《史记》究竟有多重要?
李开元:我们说读经典,最重要的是要读《史记》,因为《史记》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不读《史记》,就无法了解我们的文化基因。这些年有大量文物出土,但它们没有动摇《史记》的基本框架,而且《史记》是3000年的通史,其中的缝隙非常大,无论放多少东西进去都填不满。所以先把《史记》读通了,有一个基本框架,然后再吸收新出土的文物知识。这是一个捷径。如果读原文有难度,我建议你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正宏老师的书。陈老师已经出了三本讲《史记》的书,他讲得很好,浅显、专业且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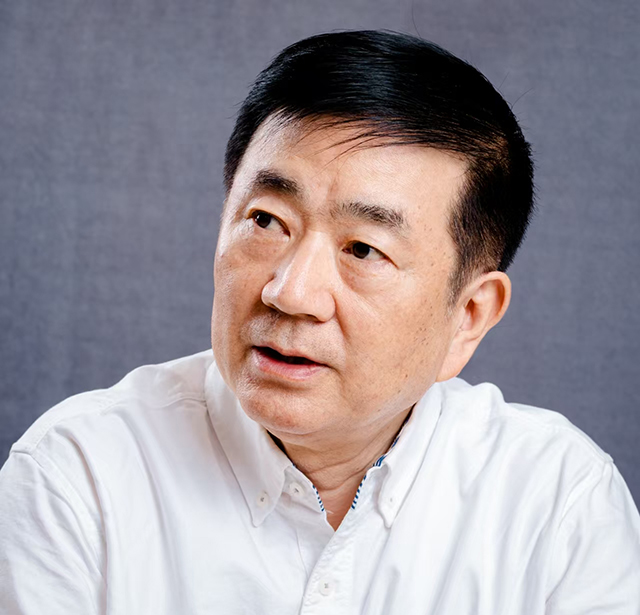
历史学家李开元。受访者供图
▎链接
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致力于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的结合,追求打通文史哲、科学与艺术并举的新史学。主要学术领域为战国秦汉史与史学理论。
主要著作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等。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