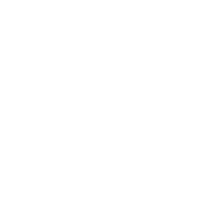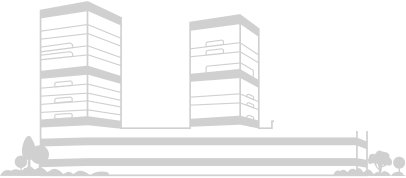【文/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在上海的街角,偶然一瞥,或许就会与大唐相遇——梧桐掩映的弄堂口,身着襦裙的少女翩然走过咖啡馆外窗;新中式茶馆的屏风后,茶筅打出细腻的泡沫,香气四溢;新潮的餐馆里,就餐像参加一场Cosplay,胡旋舞正踏着千年的节拍。这座城市仿佛与唐风余韵有种隐隐的共鸣:那种奔放雍容、海纳百川的美学气质,从未真正远离,只是在玻璃幕墙的折射下,变换了姿态。
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对一个辉煌朝代的表面模仿,而是一种深入精神的辨认与追寻——在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对精致生活的执着追求,以及将外来文化化为己用的创造中——在上海,大唐能看见千年前的自己。大唐之美,炽烈雍容,有容乃大。以至于千年之后,它依旧能在这座现代都市的街角巷陌绽放,并激荡出如此广泛的回响。
一只“飞”过千年的鹰
就在几天前,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只凌厉华美的“鹰”风头出尽。这把“三彩鹰形壶”来自1300年前的盛世大唐,估价1000万港元,结果以2294.5万港元落槌。如此天价,在艺术品市场整体不景气的今天实属罕见。当然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只唐朝的“鹰”有一种让藏家举牌不止的“魅惑”。
此鹰何“魅”之有?
这是一把壶,里面可以置酒,只是外形做成了老鹰的形象,那酒就是从凌厉的鹰嘴里流出来的。细想起来,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创作。鹰志在高远,以鹰眼看世界,其他生物恐怕都是“井底之蛙”。可将其做成酒壶,“玩鹰于股掌”,鹰就成了一只被驯化的宠物。
有专家说,这显然是受了盛唐时期开放包容氛围的影响。当时唐都域外胡人遍布。胡人架鹰抱犬、带豹驮鹿的生活消遣方式吸引着唐人的目光。唐玄宗在位期间,宫廷专设鹰坊,蓄养猎鹰与猎犬,此件鹰形执壶即可能制作于这一时期,是汉胡文化碰撞的产物。
另一点必须点明的是,此“三彩鹰形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作品。唐三彩应该是唐代最有名的瓷器品种了,直到今天仍如雷贯耳。唐三彩实为一种上釉烧制工艺。像那件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国宝“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便融汇了蓝、绿、黄三种单色釉,瓷器烧至800摄氏度时,釉料自然流淌融合,形成变幻莫测的绚丽艺术效果。
此“鹰”的三彩是褐、绿、白三色,相比“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釉色的洒脱融合更为自然。当然,这并不是说匠人对流釉不加干预。最后呈现的效果是鹰的翅膀处为亮丽的绿色,肚腹以白、褐为主,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器物的立体感和雕塑感更加突出。
“国富艺强”,当美成为日常
现在可以由“三彩鹰形壶”来对“大唐美学”进行少许总结。其一,这肯定是一种“包容之美”——来自西域的鹰,成了唐人桌上的壶,这种跨越万里的对话,显示了当时文化交融之盛。其二,这肯定是一种“华丽之美”——让三种饱和度颇高的单色釉自由流淌、交融,如同后世张大千的泼墨山水,如此洒脱,随性之中又透着艺术的“心机”,这样的美不华丽才怪。
说到底,所谓“大唐美学”是一种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的美学。在唐朝之前,那时的饭碗、茶杯,那时的服饰、铁器基本上做出来还是为了“用”。即便是做工精美的青铜器,也是一种礼器,为了祭祀之“用”。而唐朝人似乎就有点不同了,他们的器物固然还是要“用”的,但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此,还想着再美一些,所谓赏心悦目。用现在的话说,唐朝人开始想着要给器物增加“情绪价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大唐之美》一书指出,在唐代,这样“无用之用”的美遍地可拾。唐代的绘画已到一个高峰,吴道子、阎立本、张萱、周昉等画家已创造了一个精绝的“纸上世界”。书上说,当时绘画写实性增强了。不过,写实之外更有写意。吴道子之画有“吴带当风”的典故——吴道子画中女子身上的绸带随风扬起,这需要何等写实兼写意的功力。
唐人服饰则更值得一品。唐初女子时髦的装束,上身是窄小的衫或襦,下身为束裙,肩加帔帛,裙高腰束胸,宽摆齐地,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帔帛长而宽,使用轻薄的面料,随意披搭,像一缕飘扬的烟雾,恣意挥洒着女性柔丽轻盈的身姿。而唐代后期“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流行宽松肥大的裙子,被歌咏为“裙拖六幅湘江水”,表现另一种潇洒的风度。
阅读唐代史料,很容易被一种强烈的感受冲击——千年之前的唐人为了美可谓煞费苦心,甚至有点无所不用其极。追求美,俨然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使命。当然,在古代文化研究学者奚林看来,这就是所谓“国富艺强”的最佳注解。只有当国家富有了,人民的温饱解决之后,对于美的那种渴望和追求才会一点点浮现出来,不可遏制地生长。
照见古今生活的密度
虽然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令很多风光一时之物湮灭于无形,但今人依然对“大唐美学”情有独钟,甚至一说起此,便生出一份遥不可及的崇敬。之所以如此,答案并不复杂,那是因为“大唐美学”已渗入当下生活的肌理。
如果说器物是凝固的美学,那么技艺便是流动的传承。大唐之美,不仅存在于博物馆的展柜中,更复活于当代人略显笨拙却满怀虔敬的实践里。
记者曾应约参加过一次茶会,只是那次茶会焦点不在于茶,而是茶百戏。唐人喝茶和今人不同,唐人不泡茶,而是把绿茶磨碎了,置于茶碗或建盏中,冲入热水,用竹制的茶筅打出泡沫,然后就在这泡沫上用特制的竹签子作画,此为茶百戏。
那场茶会,“狼狈”者颇多。用茶筅打出泡沫的过程便是大名鼎鼎的“点茶”了。点茶者用力越是精巧,时间越是持久,茶汤泡沫便越是浓厚细腻,为下一步的“茶百戏”打下基础。可当时,点茶的先生要么用力不当,总把茶汁打出建盏,要么平时缺乏锻炼,搅拌几下便直呼“手酸”。总之,成功者不多,茶汤倒是洒了一地。
“诸位就是心浮气躁了。”茶会主人、一位深耕茶道多年的优雅女士一语道破天机。“想想一千多年前的唐人,不紧不慢地点茶,一边点茶,一边为茶百戏打腹稿。茶画往往一挥而就。随着泡沫慢慢消逝,茶画也随之变幻莫测。”
茶百戏虽然盛于宋代,却始于唐代,唐人对于美学的极致追求,才造就了这种令今人“望茶兴叹”的玩法。在茶百戏里,唐人欣赏的,正是这种瞬间的、不可挽留的美。这是一种关于“逝去”的哲学游戏。“茶百戏是一面生活的镜子,过去古人可以玩得很洒脱妥帖,今人就已经难以驾驭了,这可以看出今天的生活已经把人‘折磨’得有点粗陋了。”茶会主人对记者说。
的确,茶百戏这面镜子照出了前人可及、今人无力,此时不免要想一想各种缘由了。有时为了思考自己的生活,就应该多树几面这样关乎“大唐美学”的镜子。记者曾采访过一位高古瓷器的收藏家,他对清代那些纹饰工整的官窑瓷器全然提不起兴趣,对清末所谓细路粉彩也是敬而远之,却唯独对唐三彩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每次看到这些千年前洒脱的艺术品,他就会扪心自问:当下的生活,洒脱否?松弛否?
胡旋舞配海鲜羹,上海对话大唐
唐代兴盛时期的中心长安和东都洛阳离上海都很遥远,而且唐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上有名的大城(上海的青龙镇要等宋朝时才兴起)。但是让人称奇的是,上海与唐朝,与所谓“大唐之美”之间似乎有一种惺惺相惜。
上海人对于大唐之美的热爱是毫不掩饰的。记者曾去一家汉服摄影工作室采访,主理人告诉记者,他们提供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的汉服给客人选择,虽都叫“汉服”,但大家选得最多的还是唐风服饰。记者问为何,主理人想了半天说:“也许上海当下的繁华,总让人想起唐代四衢八街九陌的繁华。这就是一种心灵映照了。”
在上海还有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馆,食客入席前必须换上唐代服饰,女服务员也是一袭唐代装束,吃饭就像一场Cosplay沉浸式体验秀。席间高潮,便是一曲胡旋舞。用薄纱蒙了半张脸的舞者,在食客席间优雅翻飞,令人目眩神迷,给食客带来“梦回大唐”的感觉。
胡旋舞确实盛行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本来是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舞蹈,后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中原,逐渐成为唐朝宫廷教坊杂舞的代表性节目,广泛流行于宫廷宴飨及民间活动。所以在宫廷菜馆子看胡旋舞是十分贴切的,只是那所谓宫廷菜以海鲜羹闻名,这就十分“可疑”了。因为唐朝宫廷远离大海,海鲜一定不是经常可见之物,所以“胡旋舞配海鲜羹”多少有点“混搭”的意思。
对于这种时空错位的搭配,奚林先生让记者不要过于较真。“大唐之美的一个要素就是开放和包容,现在用胡旋舞配海鲜羹就是点了‘包容’这个题。”奚林说,他觉得这恐怕正是唐朝和上海如此契合的原因。如果时空可以穿越,那上海人爱唐朝,唐朝人也一定会爱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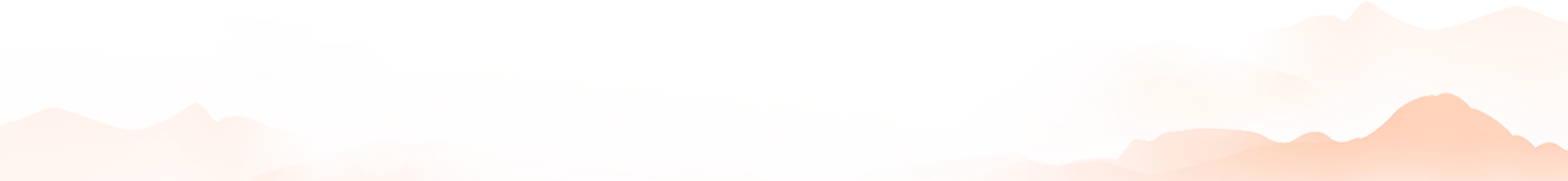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