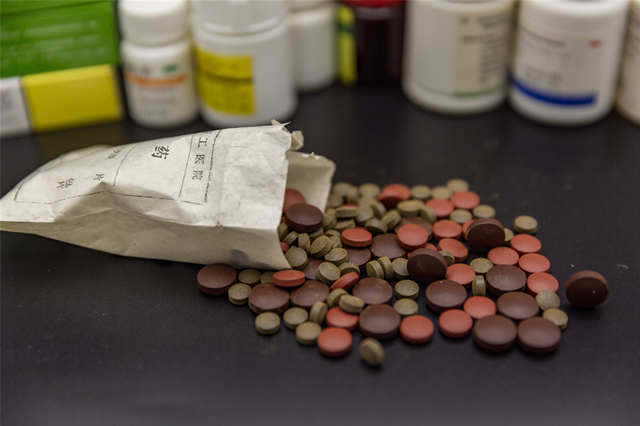14岁以下的“触法未成年人”如何处理?上海开始这么尝试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陈嘉音
触目惊心的“小学女生校内遭4名男生侵害”事件,再一次让未成年人犯罪进入公众视野。近几年,对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事实上,14岁以下的“触法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无责犯罪儿童)如何处理,成为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道难题。
6月,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启动了违警触法未成年人工作试点,开展触法未成年人群体的即时转介与跟进服务机制,探索未成年人司法与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整体性前移。
案例
“触法未成年人”群体不是少数
“如果之前有人管管我,如果我早知道会这么严重,我就不敢这么干了。”冷冷地说完这句话后,因盗窃行为被刑事拘留的小Z低着头不愿再交流。目前中国青少年犯罪已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布数据显示,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2.2岁。
幼时母亲患抑郁症自杀、父亲身体不佳、单亲家庭亲子沟通不畅、亲戚抚养,在典型的家庭监护缺失困境儿童成长环境下长成的小Z早在刚进入初中阶段时就出现了初次不良行为。从最早的旷课到逃学,再到辍学、夜不归宿、染发、纹身,家庭和学校的正常管教对小Z已经很难起到作用,他的不良行为逐渐严重。
15周岁时抢包、破坏公物因年龄尚小而免受处理,肆无忌惮的小Z半年后实施盗窃行为时却没有能够再次免于处理,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他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办并进入司法程序。事实上,像小Z这样曾经触法未受处理后又再犯的未成年人并不在少数。
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下触法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屡屡出现,引发社会广大关注和热议。但在这些极端个案之外需要重视的是案情并不严重但整体数量无法确认的,实施了犯罪行为却未受处理的“触法未成年人”群体。
现状
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升
6月1日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上升态势。涉未成年人犯罪稳中有变、司法保护任重道远。
未成年人小燕同样来自一个复杂又残缺的家庭:母亲因不堪忍受吸毒的丈夫,怀着孩子起诉离婚,却不想在远离了苦海后,又一脚踏进了另一个牢笼。现任丈夫不仅以贩养吸沾染毒品,而且还有严重的家暴,这就是小燕的家。年幼的小燕就这样在母亲的无奈、祖辈的嫌弃和继父的厌恶下,受着家暴的耳濡目染慢慢长大......
如今的小燕才七年级,但已有过多次逃学逃夜、聚众斗殴的行为。被多次家暴过的她不管在外界遇到什么事情,都以暴力解决问题,因此她多次在学校伤害同学,并制造了几起校园霸凌事件,那份扎根在心底最原始的暴力已然慢慢融入了她的生活,变成了习惯。随着矛盾越发僵化,小燕后来便辍学了。
《白皮书》通过对近年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况进行分析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未成年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上升;同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不容乐观,性侵害、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成年人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黑恶犯罪等问题相对突出。
探因
在监护缺失或不当的困境家庭环境长成
作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为代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十六年来累计为超万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在构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依托十余年来的素材积累,我们研究发现,除少部分冲动等因素导致之外,80%以上的16至25周岁的涉罪青少年早在他们初中阶段前后就开始滋生初次不良行为。因此他们的犯罪行为产生有其必然性存在。”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信息管理主任张瑾瑜表示。
大部分涉罪青少年都是在监护缺失或不当的困境家庭环境长成,家长的价值观、行为本身就会对孩子造成代际传递的影响。
在小升初后,这些监护困境的孩子面临环境、同学、学业压力的巨大变化后,因为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很容易因为无法适应而滋生例如旷课、逃学等初次不良行为。之后如果没有来自家庭或学校的有力监管,这些原本程度尚轻的不良行为就会逐渐严重,极有可能演变为违法或触法行为。
“如果等他们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和情节的要求进入司法程序再介入,社会工作者也已经很难挽回这些人生观、价值观早已固化了的孩子们。”张瑾瑜说。
难点
如何化解困局
当前,我国对于这一群体依据相关法律确立了数种措施予以帮教,但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这些措施均难以有效发挥其作用,从而导致触法未成年人实质上大部分处于失管状态。
对于司法机关来讲也只能被动无奈地陷入困局,即只能等到触法未成年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可以刑罚处罚的程度,由刑法予以处罚。
上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课题组专家、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问题》编务主任田相夏告诉记者,真正的难点在于干预措施不到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闭环。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会有苗头:比如在学校里小孩子打人、欺凌,但现在学校、社会并没有一个很好承接措施。“假如一个班级里,排名后10位的同学存在不良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老师不敢去管,也不会去管,因为我们缺少一套有立体化的惩戒措施。在家庭里也是一样,未成年犯罪的很大的根源来源于父母,父母的恶劣行径影响了孩子,受到影响的孩子有了不良行为,也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干预,就这样形成了一条矛盾链。”
专家表示,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惩罚并不是目的。“就算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要出来的,我们要保证他的教育,要有一技之长。”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要遵循双向保护的原则——既保护未成年人,又保护社会利益。当前社会上广泛议论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是引入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举措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尝试
违警触法未成年人群体研究项目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关键时期,当大家都聚焦、争论于究竟是降低刑责年龄还是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时,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开始探索如此一条崭新的途径。
6月,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启动了违警触法未成年人工作试点。试点项目得到了相关区政法委、团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将以试点形式在徐汇、长宁、杨浦、青浦、崇明、奉贤六区,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与公安机关之间对于实施了违法或犯罪行为但因责任年龄或其他法定原因免受处罚的未成年人群体的即时转介与跟进服务机制,探索未成年人司法与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整体性前移。
试点同时将以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行为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此为监护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和以不良行为学生为对象的联驻校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和介入角度。
“社工的介入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在专业性上要高于父母与老师。在未成年人犯罪干预中,社工是第三人,是家长和孩子沟通交流的纽带。”田相夏表示,未成年人司法与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探索,有利于触法未成年人群体工作的开展。
在开头小燕的案例中,社工一方面充分调动母亲的责任感,让她更多关注和鼓励孩子,一方面在心理层面加大对小燕的支持力度,逐渐缓解她潜意识里面的暴力倾向,相信随着亲子间的沟通加强和社工对这个家庭注入的点滴之爱,这份助人的真情会慢慢渗透到小燕的心灵,终有一天她也会迎来人生的新一轮曙光。
>>>Tips:
未成年人司法和社会工作的发源地
上海是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发源地。1984年,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启了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征途。2003年,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开始探索以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陈嘉音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