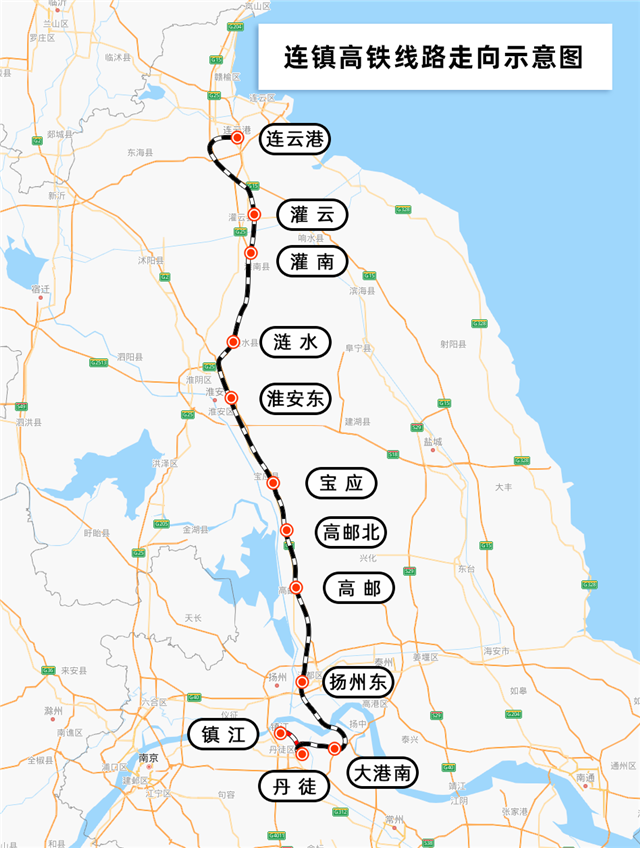漫话“角色I、II” ——为2020年第九届“百川奖”作曲比赛决赛音乐会而写

2020年12月,上海音乐学院“百川奖”作曲比赛的举行,让校园里充满了无限的新生能量,11个年轻的声音在这一晚相互一较高下,但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比赛,11个不同的个性理念,正尝试着打开音乐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作曲者”身份的两种转换,使得我们站在角色式的立场之上,去接收这些“迷茫”可却具有裂缝气质的音乐。
角色I “间离者”
混合室内乐编制(笛、二胡、琵琶、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比赛要求,奠定了“间离者”的角色基础。这里的“间离”,更像是布莱希特式话剧舞台上的演员,承担着“间离”观众的角色。布莱希特的“间离”,通过借用戏剧自身以外的“角色”——说话人,使得观众对戏剧表演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变得更加冷静。决赛中的11首作品都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理念:波兰作曲者托马斯而•斯尔克帕尼克的《Tessuto 2》里,二胡在一种成熟的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基础之上,作为类似说话人的“间离者”,在与西方乐器之间艰难地搭起一座桥梁。
而我们说,“间离”总是“跳进又跳出”,从本有的戏剧身份角色中脱离出来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二胡这件乐器,在这首作品中,似乎以一种无法抽离的“间离”状态,迷茫地打着碎弓,而在相异语境下,与弦乐器的打弓产生共鸣,这又是一种“落入”。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毛宇轩的《黑风——为八件混合室内乐而作》中,三件中国乐器共同参与着“间离者”角色,但在此之中,箫从作品伊始的气声,到终了时的气外之音,一种通过积聚演奏者所有能量的吹奏,引起听众感到晦涩与生理极限的承受,这种极端的神经刺激,也放射出所有新作音乐的强烈信号,我们如何去转化音乐所带来的身体挑战?
角色II “思考者”
接续上述“挑战”话题,是否意味着新创作者与听众,都需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一种转向“思考者”的角色状态?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学生姚雨霁的《楚山孤 II》中,对琵琶声响的美学转换,以一种打击乐器的姿态去融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文子洋的《流影》中,对竹笛声响的“去表征化”尝试,来呼应“震音”的声音属性;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太古的声音》中,对于小提琴碎弓音以及琵琶如自然响音般的轮指音,不作多余而无味的人工修饰;中国音乐学院学生毛宇昂的《一念》中,二胡在极高音区艰难拉出的哑音式乐声,虽显极限,但也由此刺激出听众的生理性思考。
这些作为“弥补古典音乐对人类理性思考缺憾”的重要技术语言,似乎让作曲者和听众都成为了不可不思考的“思考者”,而这是否成为当代新的音乐作品,最独特、最具能量的正向结果。当声音本体难以突破自身形式语言之时,这种由内而外的刺激属性,让我们对新的音乐有了更多期许。而这是否又是当代音乐通过其自身的内在肌理,对人类本有属性(这里特指“思考”)的一次变革,成为文化、艺术中最抽象但也最直接的思考路径?我们不再受限于地域、民族、艺术种类,关于自然、时间、生命、爱的思考,都在一种日趋成熟,具有“瞬间性”的当代音乐技术语言里得到释放。
回顾角色I、II,当代新音乐的独特属性,在探讨其自身与听众的抽象关系里解脱出来。比赛决胜作品——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刘欢的《竹林与水田》中,四件弦乐器对作品速率的掌控,既有点线块面式的声响追求,也有“泼墨”样态的直观显现,竹笛对旋法的突破是水墨的运动样态,而琵琶的大小轮指、扫、弹技法,奠定了它作为与刺激声响相抗衡的基础乐器,同时声音的“间离性”自然产生,使得听众得以从中窥探出自由而非无章的合理“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 吴洁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