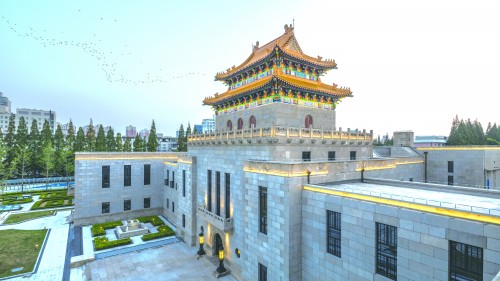品读|钟求是的那一面

□哲贵
一
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多义的。诡异的是,我们看人却是片面的,只看某一面,也只愿意看某一面。很多人对钟求是的认识也是如此,认为他认真,较真,不圆通,甚至有点古板。不可否认,这些特点他身上有。可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身上另一些宝贵的品质,譬如他对世俗的抗拒,对底线的坚守,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包括对人的宽容。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面镜子,从他那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和犹豫。但我不想在这里表达求是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正是大家认为的那一面。
忘了什么时候认识钟求是。我这里所说的认识,指的是第一次见面。我怀疑是在一次乱哄哄的酒场。喝酒的场合总是群情激昂的,气氛和身体是热烈的,甚至是沸腾的,特别是进入后半程,整个酒场处在颠簸和飞翔状态。那个世界是变形的,也是失真的。等到次日酒醒,很多事情已经变得影影绰绰、若有若无了。所以,在酒场上,人与人交往是可疑的,那种速度和热度,是通过巨大的外力推动的,是身不由己的,带有很大的想象和虚拟成分。但求是不是这样,即使身处波涛汹涌的酒局,他依然是冷静的,依然保持着应有的清醒,在这方面,他是讲原则的,甚至是“残忍”的。2020年12月6日晚上,我们在富阳举办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的前一晚,求是和我请一众朋友到一家温州人开的海鲜楼宵夜,喝到12点,大家酒兴调动起来了,海鲜鲜美,气氛蓬勃,主要是喝酒的人对路,大家正准备放飞自己,这时,求是举杯站起来说:晚上就到这里吧,明天一早还有活动呢。好了,钟主编踩刹车了,大家意犹未尽,但是,从某种程度说,意犹未尽就是没有尽头的意思,那就散了吧,明天还得起早呢。我想,如果是我,肯定刹不住车,是舍不得刹,根本不想刹,我已经飞起来了,哪里还管明天的活动,喝了再说,喝倒几个算几个,明天的活动明天再说。但求是不是这样的,他在这方面是清醒的,是理智的,孰轻孰重是拎得清的,该踩刹车的时候,他绝不脚软。
这估计是求是给大多数人的印象,似乎他的内心收敛着,尚未向人敞开。我想,于他来讲,这未必是一种刻意行为,可是,对于他人而言,在与求是交往过程中,便会产生距离,甚至偏见。
其实,我有时想,求是给人这种印象,也不全是他性格上的原因,这可能跟他曾经工作了十五年的单位有关,跟他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不是他时刻在保持清醒和距离,或许,在很多时候,是别人有意无意中将他“定位”了。
那时候,我们都生活在温州,他在特殊的涉外部门工作,是某个重要处室的头头。我认识求是的时候,他还没有调到文联,可能正在调动,因为文章开头说的那次喝酒,一个主要议题便是他为什么要调到文联。
我听说,组织找他谈话时,他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另一个系统当副手,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部门,但从仕途晋升的角度考虑,是更具有可能性的。求是大学学的是经济,经济是理性的产物,是讲逻辑的,是讲实效的,是权衡得失的,再加上十几年在特别部门的特殊训练,理性已经成为本能,也就是说,到文联上班,于求是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是一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
放弃好的仕途单位,这不符合逻辑,至少从世俗的目光来看,不符合一般人对职业的选择。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个逻辑在求是这里是成立的,这种职业选择在求是这里是必然的。往小里说,是一个人的性格,往大里说,就是命运。
二
求是到文联后,我们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所谓的频繁,就是经常在一起喝酒。坦率地说,求是的酒量很一般。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在一个温州作家作品研讨会之后,我们一堆人喝散伙酒,喝得兵荒马乱,谁也没有注意到求是和吴玄,好像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酒量,两个人把杯“干上了”。我估计二两半白酒下去,他们对真实世界已经失去了判断,不计后果了,所以,又各喝了一些,求是不记得是我送他回家了,到家后,他爱人给我打电话,说求是回家后,嚷着要她陪他继续喝酒——不喝不行,态度相当坚决。当我赶回酒店,吴玄已经趴在洗手台上吐得不省人事了。以酒量计,求是大概是二两的量,但他不排斥酒,据说每天在家晚餐都会喝上一盅,大概一两。出去开会,喊他宵夜,他都快活参加,如果自己单位举办活动,他还偷偷从家里带酒出来。 在温州,很多时候是三个人喝,除了求是和我,还有一位徐建宏。徐建宏专攻葡萄酒,以喝啤酒的姿势喝葡萄酒,以把自己灌醉为目的,是酒中豪杰,从来没把我和求是放在眼里。求是是一贯的低调,只喝啤酒,我偶尔陪徐建宏喝一两扎葡萄酒,最终还是换回啤酒。如果是我和求是两个人,肯定是喝啤酒。他对啤酒只有一个要求:酒精度越低越好。而我恰好相反,酒精度越高越好,即使是冬天,我也要喝冰镇啤酒。我和求是喝酒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一,其实,两瓶以后,他的节奏就跟不上,酒局绝大多数是以他喊停而告终的。
在文联这段时间,求是写出了一系列使他名声鹊起的小说,有《秦手挺瘦》《谢雨的大学》《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两个人的电影》等等,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零年代》。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是不满意的,觉得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作品,他有目标,也有信心,可又有点迷茫。这可能是他离开温州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主要原因吧。2009年,他离开了工作十年的温州文联,调到《江南》杂志社当副主编。
十多年过去了,求是跟温州文联的老同事依然保持来往,过一段时间,便会约起来聚餐一次。如果有温州文联的老同事到杭州开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宴请。在这一点上,求是显得特别念旧,特别重感情。这体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并不总是在克制自己,他内心有特别柔软和主动的部分,只是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而我在不同场合听到温州文联的老同事说起求是,也都是赞美之词,说他办事认真、负责,说他对待同事真诚、善良,说他如果继续在文联待下去会如何如何,总之,对他的调离是不舍的,是充满感情的,差不多是在追忆美好时光了。
三
说起来,我和求是真正交往应该是他调到《江南》之后。也可以说,这时,我才开始真正认识求是,这里所谓的认识,指的是对他这个人的了解和理解。这么说有点伤感情,也对以前的历史不负责任,十几年的交往都干什么去啦?都是吃吃喝喝啦?仔细一想,确实如此,因为同处一城,见面机会多,住得近,除了偶尔交流一下最近所看之书,还真是以吃吃喝喝为主,每次见面都是在嘻嘻哈哈中愉快地度过的。
实事求是地讲,求是的朋友不多,他对朋友是挑剔的,是绝不含糊的。我想,只有内心极端珍惜朋友的人,才会对交往的朋友精挑细选,才会像选老婆一样选择朋友。他在昆阳老家有几个少年朋友,是从小学就开始交往的,他每次回温州,只要时间允许,昆阳是必须去的,而且要住一夜,跟那些朋友喝顿酒,吹一次牛。他这些少年朋友我都见过。大约是2018年初夏,求是的小说集《昆城记》出版后,应邀去老家做新书分享会,我去站台。我在台上一坐,发现前排几位读者神态怪异,一般参加这种活动的人,都是抱着看耍猴的心态来的,那几位表面上也嘻嘻哈哈,但嘻嘻哈哈的同时又夹杂着紧张,紧张里又有期待。他们的表情特别专注,差不多是含情脉脉了。分享会结束后,我们去宵夜,席开两桌,分楼上楼下。我去楼上敬酒,开门进去,见到的就是刚才坐在最前排那几位。我当时就有预感,那几位一定是求是的少年朋友,果不其然。
我不知道他在温州还有什么朋友,但他每一次回到温州,我们总会找机会见上一面。求是爱人没有调到杭州,他每两周要回一趟温州。到了那个周末,我会短信问他:周末如果回来,一起喝个酒?有时他也会主动短信我:周末回来了,吃小海鲜去?有时我会带他去一些酒局,见到酒局上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会略显拘谨,但他是得体的,客气地接受别人的敬酒,也会主动回敬别人,至少要“打一个通圈”,这点礼数他是一定要尽到的。半瓶啤酒之后,他面红耳赤了。这是很好的保护色,他会主动说,我酒量很差的。酒局之后,我们找个茶楼坐坐,聊聊工作,聊聊近况。有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就先吃小海鲜,再去喝茶。因为见面的机会少了,话题便会涉及人生深处。当然也聊小说,聊他新写的小说,聊他耗费两年心血完成的最新长篇《等待呼吸》,聊这个小说可能的命运。
四
当年喝酒的时候,我没有料到,有一天会和求是成为同事。估计他也没想到。2019年7月,我调到省作协,2020年5月,调到《江南》。这时,求是已经当了六年主编。
关系不一样了,成了同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了。这种关系是危险的,因为是朋友,又同是写作的人,现在成了同事,成了上下级,距离缩短了,可以回旋的空间缩小了,也就是说,很多问题无法回避了。譬如对一篇稿子的判断,好还是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其实不是一篇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人文学观的问题,甚至是两个人世界观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求是肯定想到了这一点,所以,2020年5月25日下午,作协领导将我送到杂志社时,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求是在那个会议上说,我对哲贵是信任的,对他的文学判断是信任的。我听得出来,这话是讲给大家听的,也是讲给我听的。
事实确实如此,在此后的工作中,求是完全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好的稿子,他基本认可。有时,我们会同时看一个稿子,然后一起分析优缺点,商量用与不用,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主编和作家,也是读者。他是开阔的,是可以商量的,是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的。同时,在编稿过程中,他的认真和讲原则也完全体现出来。他每个月会收到很多稿件,有些是自由来稿,有些是朋友的投稿,到了双月下旬,他会将这些稿件打包给我,让我分发给编辑,再由我写了审稿意见给他。我知道,有的来稿者是他的朋友,而且是知名作家,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况下,我基本会将稿子送他终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在他的朋友来稿中,他没有签发一篇可用可不用的稿子。要知道,坚持一次两次是容易,而杂志的编辑与出版是长年累月的,这是最考验人的品格的。我想,《江南》这些年质量与口碑稳步上升,与求是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一份杂志,松开一个口子是眼睛一闭的事,守住一个口子却需时刻睁大眼睛。做人何尝不是如此?
(哲贵,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等。)
哲贵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