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宏兴,在宁静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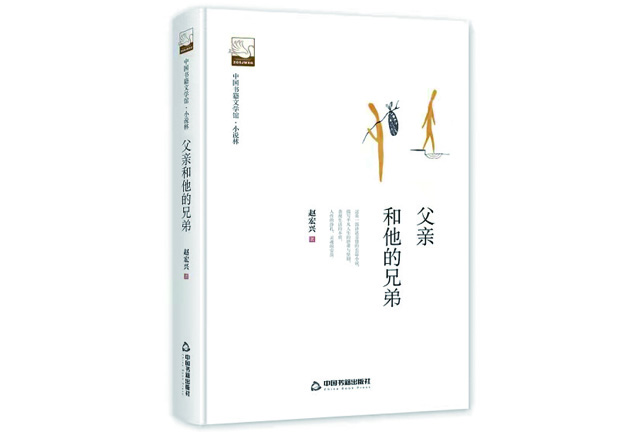
□胡竹峰
2003年前后吧,在报纸上断断续续看过一些赵宏兴的文章,写的是亲情,看得出来是真人真事,看得出来有真实情感,很朴素,很周全,遣词造句稳稳妥妥。几年后,我去了郑州工作。那时候周末得空照例去书摊看看,有一回看见赵宏兴签名版散文集《岸边与案边》。拿起书翻了翻,勾起少年的阅读旧事,也就买回来了,不愿意看见一个作家的友谊在旧书堆里被人挑挑拣拣。
《岸边与案边》写的都是家常事,说的也是家常话,老到、从容。
再后来,我回安徽工作生活,认识了赵宏兴。各类笔会各类采风大家常见面,偶尔还会相逢在饭局上。那几年,交朋友的兴致淡如残茶,也就没有和他火热,而宏兴的性格为人,望之整齐严正,也不是火热的做派。但我供职的报社每每有些文学活动,总会想起宏兴,请他来写一篇文章,请他来说一段话,以壮声威。有空他就来,倘或无暇出席则是很歉然的样子解释原由,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老派,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有回宏兴主动找我要过一本书,大概是说我散文如何如何好之类,选了本散文集《豆绿与美人霁》与他。送了也就送了,并无下文。后来再遇见,宏兴主动说请我有空给他供职的《清明》写点文章。一来我写得少,二来不太想在本省报刊发表太多作品。自然也无下文。
前些年我写戏剧系列散文随笔《击缶歌》,陆续有三五家杂志刊出,宏兴看了,说很喜欢,让我给他一组。以为是客气话,他却催了几次,我将文章发去,果然很快刊登了,不必细表。收到杂志,卷首语中一段话让我惊讶也让我受用。受用不是因为承蒙抬举,而是文人间的一份懂得。
“胡竹峰的《击缶歌》以民间戏曲为线索,于嘈嘈切切中书写一方文化,文字灵动,文采清俊,在散文的深度和厚度方面均有令人欣喜的开掘。”以民间戏曲为线索书写一方文化,这话让我有知者之遇,而文字灵动,文采清俊,开掘散文的深度和厚度云云,我都不敢当,只能算作朋友的一个拥抱,人生总是在泄气中鼓励着负重前行。
古人早就说过文人相轻,宏兴身上有文人相亲一面,让我大有好感。每回见面,从来没听过他谈论起谁的是是非非,人有兴趣的永远是办杂志,谈文学。我的话不多,他的话更少,但说起文学,宏兴偶尔也滔滔不绝,遇见不同的意见,甚至会径直争一下,羞涩地红着脸谈自己的观点。他的声音不快不慢,音调不高不低,永远不会据理力争,却也绝不妥协,哪怕退让也坚持己见,还能在他脸上看见若有若无的不平。
宏兴身上有羞涩,我觉得羞涩是好品质。不独羞涩,还有内敛,内敛更是好品质。
宏兴早期用过一个笔名“红杏”,我以为好。文学本是红杏一枝出墙来的事情,还常常墙里开花墙外香。如今换回了本名,宏兴就是宏兴,本名也好。《说文解字》上说:“宏,屋深响也。”兴,兴致,兴会,兴盛。这么些年,宏兴编辑、写作,有诗歌、小说、散文、随笔,一本接一本,兴致勃勃又不动声色。见多了众声嘈杂、大张旗鼓,难得有人不动声色。
宏兴是肥东人,肥东是包拯的故乡。宏兴身上似乎有包拯的影子,不苟言笑,对文章铁面无私。偶尔见一些作家给他写稿子,他总是客客气气收下,但具体到作品得失刊用,自有规矩。这么多年他编辑《清明》,固守叙事,固守现实主义传统。好不好不知道,也轮不到我来置喙,但凭那一份韧劲,值得喝声彩。
见过一次宏兴的豪气,是他敬业的一面。那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宏兴来北京组稿。他让我张罗了十来个作家,大家喝茶聊天,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末了宏兴请大家吃饭,去的是新疆菜馆,烤肉丰美,大家团团围坐,宏兴难得有谈兴,说了一些文事。后来果然有一些人的作品在《清明》刊登,这事让我很感动,《清明》并不缺好稿子,我们那一次读鲁院的都是年轻作家,宏兴不薄新人,这是他的厚道与热情。
记得宏兴说过,宁静的地方,空间才会开阔,思想才会自由,所以他的散文不喜欢往热闹处写,喜欢往宁静处写。他编杂志写小说都是安静的,他的小说多是乡野天空下的悲欢离合,多是篱笆黄昏早霞云朵的故事。由文到人,宏兴为人也宁静,这是我对他文章与人的印象。另外的印象是性格不算风趣活泼,但低调温和,对事又严谨又认真,做人宽厚朴素。日常晤对接待,他的表现,用古语说是诚和敬,没有锋芒,话多是发自心腹,和和气气,这样的人如今不多的。
(胡竹峰,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雪天的书》《竹简精神》《不知味集》《茶书》《民国的腔调》《击缶歌》《雪下了一夜》等散文随笔集二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红豆文学奖、《广西文学》年度优秀散文奖,《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胡竹峰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