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编辑与作家,我一辈子喜欢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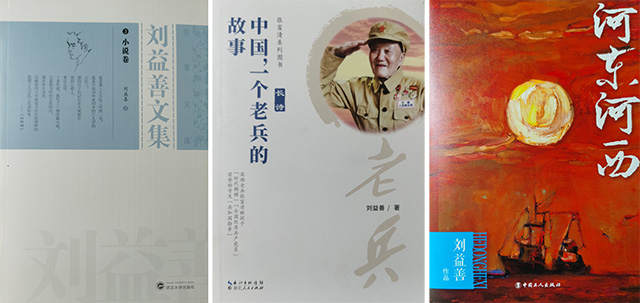
□刘益善 陈智富
陈智富:刘老师好!您说过“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您是编辑与作家,您说说最初的文学启蒙好么?
刘益善:智富好。编辑与作家,是我这一辈子喜欢做的事。我出生在乡村,从小喜欢听说大鼓书,从五六岁时就开始听。我在乡村的茅屋里,听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刘子英打虎》《封神演义》,等等。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读《说岳全传》《牛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我那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乡村说书人。这大概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陈智富:您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什么?看到自己的文字发表,当初的心情是怎样的?
刘益善:1969年,我已从中学回农村当农民了,生产大队让我写节目,我就写了《亿万人民庆国庆》,四句一段,押韵顺口,便于演唱。那时武昌县有一本油印杂志《武昌文艺》,我把稿子投给他们,他们就发表了。邮递员把发表我作品的油印刊物送到时,我正在大田里割晚稻。我看到我的诗出现在刊物上,虽说是油印的,但那心情是激动的,心里就决定我要写作。
陈智富:您后来是怎么走出乡村上的大学呢?
刘益善:1971年初,贫下中农推荐我去读大学,叫工农兵学员。我被推荐去的学校是华中师范大学,专业是生物系。招生老师把武昌县即将上学的学员,集中到县城纸坊学习。这时,我找到招生的老师,要求上中文系,希望毕业后能当作家。招生老师一句话打发了我:服从分配,不能挑挑拣拣。
就在我失望之际,一个机遇到来了。招生的老师说,要在我们这些学员中挑一个人,去采访武昌县新屋公社叫程光桃的妇女,写一篇文章。招生的老师向大家问了三遍,没有人应声,最后我勇敢地站起来说:我去写。
我采访了程光桃,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农妇。程光桃的经历和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非常悲惨。我的文章招生的老师看了后,说这孩子不上中文系可惜。于是我就上了华师中文系。
在华师,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被那满架满架的书惊得呆了,我不努力这些书读得完么?于是我拼命读书,第一次放暑假,我背了二十七本书回家读。读书开阔了我的眼界,读书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更加坚定了我追求文学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七一届华师中文系学生出版了一本《春苗茁壮》的小书,收了我的四篇作品,有小说有诗歌有评论,是收入作品最多的。我在华师时,是那一届中文系第一个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的人,文章都是老师拿去发的。
陈智富:您在文学道路上,遇到哪些对您影响很大、帮助很大的前辈?
刘益善:到了工作岗位上后,《长江文艺》老一辈编辑言传身教,使我做人做文学走正路。要说在文学上给我巨大影响的,是徐迟先生。我在紫阳路住在二楼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徐迟从干校回来,住在一楼,他经常到我的小房间聊天,给我开书单,给我修改诗歌,给我写了好多的信,都是谈的诗与读书。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徐迟先生亲自做介绍人。我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1981-1982年《诗刊》奖时,先生已搬到水果湖高知楼,他从家里打电话给我,一是祝贺,二是提出希望。我曾经写过《徐迟先生教我写诗》的文章发表在《诗江南》杂志上。还有碧野、曾卓、王先霈等先生,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陈智富:您在《长江文艺》工作多年,退休后又给杂志当特邀编审,伴随着湖北文学走过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一代代作家的成长并走向全国,为湖北文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就您的编辑生涯,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刘益善:我1973年10月到《长江文艺》当编辑,退休后又到《芳草》当特邀编审,今年正好50 个年头。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编辑,我看到一篇篇作品的发表,一个个作者的成长,这些作品这些作者,在中国文坛各领风骚,我为他们出过力,我特别高兴。
陈智富:您写道:“我无舟楫穿越秋水/永不能到达彼岸/辜负了你的绿色/那花开得好寂寞。”这似乎为您的编辑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透射着自省和自谦。虽然,您一般不太愿意公开讲自己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哪些杰作、培养了哪些作家,总表达一个观点:“《长江文艺》是一份有着良好的编辑传统的老牌文学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她服务过的老编辑、名编辑很多,我的三十年编龄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您的编辑生涯中所遇到的哪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同时,不得不提的是,您有没有错过的哪些作家作品、遗珠之憾?有没有受到一些作者的误解?
刘益善:我当编辑的年代,《长江文艺》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发现人才,发现好作品,不遗余力地推出作家,更多的是湖北作家。老一代的编辑曾推出韦麒麟、未央、李准等一批在全国享誉的作家。新时期后,编辑部继承了老一辈编辑的传统,重点关注湖北省作家诗人。经我的手编辑推出的有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方方的《桃花灿烂》,刘醒龙的《秋风醉了》,晓苏的《三个人的故事》,等等,还有陈应松、邓一光、徐鲁、晓苏、何存中、曹军庆等人的小说散文。很庆幸,我手上没有错过作家的作品,没有过遗珠之憾。
陈智富:自从邓一光老师喊您为老哥,就这么喊开后,整个湖北文学圈都习惯这么称呼您。据说当初您三十多岁,还有点不乐意。这是不是和您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发现、培养、提携、推介了很多青年作家有关?这种亲切的称呼也体现了无数作者对您的敬重之意。您喜欢这个称呼吗?您觉得,文学编辑和作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刘益善:我当编辑有三爱:爱职业,爱作品,爱作者。我与作者的关系很好,我从底层走出来,我视作者为友,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贵贱,不论亲疏,给予他们可能的帮助。我去年到深圳领全国奋斗杯散文奖,已在深圳安家的邓一光刚下飞机,就在一家酒店订下位子,把我从会场拉去,说:“老哥来了,不吃饭怎么行?”邓一光最早喊我老哥,早就习惯了,这是他们的一种情谊。文学编辑和作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挚友。我们是朋友,但在稿件面前,却不讲私情,不放低要求。
陈智富:您是编辑,又是作家。组诗《我忆念的山村》的发表并由《诗刊》转载,后来获得《诗刊》1981-1982年优秀作品奖,应该是您诗歌创作的一个标志。据说,这是您在房县当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一年,回城后酝酿结出的硕果。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造成全国性影响?这个作品的成功给您带来了哪些创作经验?
刘益善:1977年,我被派到房县当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这一年的山区生活对我人生有着重要影响。我在平原上长大,我没有想到山区这么穷,我心里是和那些山里的农民父兄相通的。回武汉后,房县的经历在我脑海里不断地酝酿着,发酵着,我想着要写一点什么,要为房县写一些作品,于是我写了《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诗刊》转载,引起了一些反响,诗评家张同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这组诗是“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我写这组诗时,没有想到造成什么影响,就是想表达我对房县农民父兄的一种情感。这组诗给我的启示是情感发酵越久,表达出来后的冲击力就越大。
陈智富:诗歌被誉为文学王国的桂冠。很多作家写作都是从写诗开始的。您觉得作家要写好诗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刘益善:诗歌在当下中国称不上文学王国的桂冠,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曾被称为过文学王国的桂冠。现在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好诗也少。很多作家的写作从诗歌开始,因为诗歌便于抒情,年轻人开始写作都喜欢抒情吧。写好诗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敏感的心和精准表达的语言功夫。
陈智富:新世纪以来,您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作品,如中篇小说《回家过年》《河东河西》《远逝的窑厂》《巫山》,短篇《东天一朵云》等,还有一系列反映地方特色、具有真实品格的作品,如《向阳湖》等,引起评论界关注。评论界最开始对您的诗歌有较高的印象,对您的小说创作关注可能还是近年的事情。请您简单谈谈您的小说创作吧。
刘益善: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12月号上,写的乡村人物,题目还上了杂志的封面,至今已出版过八本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人民文学》《当代》《芳草》《天津文学》《四川文学》《作品》《福建文学》等国内几十家期刊都发表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国内选刊也转载过。
《东天一朵云》获湖北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芳草》汉语女评委奖。我写小说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乡村记忆和生活中的一些人与事无法用诗来表现,就写成小说。我的小说当然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我对现代主义的东西敬而远之,但我也读现代主义。
陈智富:您接受采访时谈道:“在小说创作方面,我的小说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现在发表的小说都是当年做编辑的时候写的,三十多年了,今天稍加改动,拿出去也能一样发表,没有一点过期的感觉。”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哪怕是被誉为看不出时代痕迹的花间词等极其讲究形式的文学流派亦然。但是,优秀的作家不应该臣服于时代的束缚,应该具有超越性,直抵永恒。您觉得,您的小说创作不过时的原因是什么?
刘益善:这个话我在一家刊物要我写的创作谈中说过,那时写了好多小说,因为编务繁重,发表了一部分,大多数稿就放下来了。退休后有了时间,就把这些小说改改,都一一发表出来了。我写这些小说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倒没有想到你说的超越性、直抵永恒,等等。我的小说几十年后还能发表,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写的是生活是人。
陈智富:刘老师,最后问一个问题,您还准备写多少年?现在写能给您带来什么感觉?
刘益善:我已过古稀之年,我还在写一些我觉得可写的东西,直到写不了时再停笔。我现在的写作不为获奖,不为赚取稿费,只为我的作品能给人一点有用的东西,也为我的退休生活创造快乐。
(刘益善: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1981-1982年优秀作品奖,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年度诗人奖,纪实文学《窑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奖,中篇小说《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与《芳草》汉语女评委奖,散文《飘扬在田野上的白发》获全国漂母杯散文奖,散文集《民间收藏纪事》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获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诗歌类大奖,长诗《向警予之歌》获第六届中国长诗奖,有诗文译介海外并选入中小学课本。陈智富:湖北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湖北作家》编辑。)
刘益善 陈智富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