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蝴蝶”是最后的美丽——诗集《猫的两个夜晚》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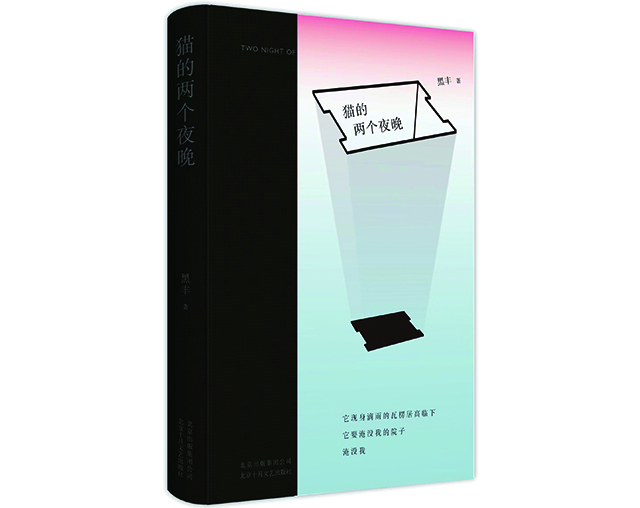
□黑丰
1993年8月的一天,我在一个随笔中写过另一段话:
年少时便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企图使一些废纸闪闪发亮。所谓废纸,即那些发黄的、一般认为不可书写的,或被人们揉搓变皱的、随意扔掉的,甚至是肮脏的。让它们重新舒展,重生,变得有味、耐看;让它们重显光辉;让人们捧着它,一遍又一遍地深入,长久地经临或驻留,久久地怀想,从而生命得以再度的升华、超脱……
这是梦,“年少”梦。
梦的核心是精神。
我是一个自始至终都有梦想的人。直到现在,这一梦想依旧,而且在继续往深处走。我不能肯定我的文字已然抵达这种精神,也不能肯定我的语言就一定使那些纸页,尤其是“废纸闪闪发亮”,但我一直在努力,笃定终有切近时。
关于“精神”或光,海德格尔也有论述:“……精神之本质在于共燃,所以精神开辟道路,照亮道路,并且上了路。作为火焰,精神乃是‘涌向天空’……”我是一只趋光的夜虫,哪怕香消玉殒。我之趋光、趋向于这种精神。
所以,在写作上,我主张从泪点到恩典,主张笔管接通人的血管,主张低温启动。永远从最低处从最冰点开始。从泪点到恩典,从恩典到泪点,往复循环。人的一生有多条路径,但一切的路径都应该是从泪点到恩典、从恩典到泪点的路径,一切距离都是从泪点到恩典的距离。
而一个诗人越能忍受自己,越能忍受困厄,便越能抵达“比早晨更早的拂晓”。善唯有在痛点的苦涩中、在黑夜的黑暗和恐怖中、在困难的困厄中、在一种非正常严冬的严寒中才是善。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画饼,善不是谎言流言不是谣言。如果善在,善就一定在苦难的泪点中,一定在最苦最难的中心承受折磨,一定在厄运的中心遭受厄运,它最低也最高;否则,它就不是善。
通往诗、诗意的写作之途永远无解。从未有现成答案。无数条路径都通向它们(通向诗通向诗意),但无数条路径都是隐匿的或隐密的,从来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对于艺术来说,所有现成的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路。世界没有捷径,所有的捷径都是你的迷径。
归零。一切皆空。这是一种感觉。完成一部(首)作品之后或开始一部(首)作品之前,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仿佛从未写作,仿佛心如处子。
什么叫归零?归零,就是回到原处,回到低地,回到泪点,回到底部。一切写作,都必须回到这里。写诗,更应这样,必须回到低地、回到泪点、回到大海的底部。
重新吐丝,结网,布阵,耕耘,收获。
回到泪点,但不是回到晦暗的盐碱地,不是回到孤绝的沙漠;回到泪点,即回到苦众之中、回到自己的黑暗里、回到一只知更鸟的午夜,去抢救一个“词”(或词根),去抢救因大雪压境濒临灭绝的梦虫和弱民的呜咽,而不是去拯救一个玩能指的“句子”,不是去拯救一篇雄文。不能让一个“词”(或词根)咯血和昏厥,不能让它们没有尊严,不能让它们冷、再冷,更不能让其沦陷和消亡于泛滥成灾的语法、指令、词牌和堆砌的辞藻中。词语正在加速堕落、异化和沙化,“词语一再碰撞冰凉的石境”。词语的尖叫就是全部。
词是什么?词是诗的“个别”细节,词中隐匿着我们祖先的眼睛。一首诗从构思一个词、从构思一种“个别的事物”(海德格尔)开始。构思,但必须体现一种词的蝶变。
词,从本质上看,它既自转,又公转;既所指,又能指;既遮蔽,又敞亮。
一首诗不是高高在上的、鼻孔朝天的。它是低俯的,诗在低地、低处;在词的根部。
有时,低处,就是高处;一切的底部,也就是一切的峰顶。
而一首诗必须是从底部涌至峰顶、从泪点涌至恩典的,并循环往复。恩典是“全部泪水都升上天空”的前提,同时,恩典也是泪点不被沙漠化、不被盐碱化的可靠保证。不然,泪水就成了人的受难的永夜、人的永远的渊薮,泪中就永远只有血腥和历难。
而每一首诗,又必须是一个又一个的“蝶变”过程。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现代诗,一次次“蝶变”。
归零,是“蝶变”的前提。蝴蝶必须回到“一棵树”,回到它的内心、回到它的根部。暗能量在这里涌动。到时说有蛹,就有了蛹。蛹化蝶,“蝶”是从潮湿的泥土、从根部、从树心飞出来的。它的光艳耀眼、摄魂夺目,它的变化无穷。它飞得像没有一只蝶在飞,飞得像一个梦幻在飞,飞得像一个天使在飞,这是一只忧郁而惆怅的蝴蝶,这是一只升空的蝴蝶,这是一只超拔于平仄和语法指令的蝴蝶,这是一只饮鸩止渴的蝴蝶,这是一只穿越《离骚》和踢踏了乌龟戾气的蝴蝶……
它的一翼向内、一翼向外,它有点玄幻,而它的身体却是处于“中道”部位的。它飞得扑朔迷离。它将飞往哪里?未知。
这就是诗。好的诗有很大的区域是未知的、晦暗不明的。

黑丰获诗歌英文翻译奖。受访者供图
一个诗人必须抽丝,结茧,成蛹,化“蝶”。“蝴蝶”是最后的美丽,但不是全部;“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想起了落叶叫喊”。“落叶叫喊”是“蝶变”的全部根据。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但仅限于“忧郁”是不够的,诗的一翼可能是忧郁的、是“落叶叫喊”,另一翼却是白日梦的,直指“前语言”。“前语言”是什么?即那种我们永远无法言说的“言说”。
我在随笔《一种地理的言说》写过一段话:
所有写作最终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指向并非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如果存在某种不可说但对人类意义深远的真实,那么,人们怎么能言说这种真实呢?不可说的怎样变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哲学家奥特弗里德·赫费提出并在他那里解决,“在此重要的是不可说的必须作为不可说的说出。‘不可说性’、神秘没有被消除。”——那么,如何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呢?
这就是诗的“深度形式”要处理的。
深度形式——“震惊”,一直是我所追求的,也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我。因为我一直追求思想的深度。其实,形式与深度并非水火不容,不是分裂的,它们是一体的;还有形式与内容也不是分裂的,也是一体的。并且,我确信:形式就是内容本身。一种具有思和启思的形式,是存在的。这种“深度形式”尽管不能一蹴而就,却能启智、引发无穷的“言说”。所以,它一直陷我于沉思之中,不敢有须臾的懈怠。
究竟如何才能创造或发现这种“深度形式”?
首先你的根须必须牢牢扎于一种“磐石之内”,这一“磐石”就是艺术的源头,“创作的起源比创作的结果来得更重要,而演变又远优于存在”(歌德),这实际上是向后看,写作总是向后的;其次是向内,向内就是朝向生命的黑暗内部,回到自身的“牢笼”,一旦我们的写作“归零”,就必须回到这里,在这里成“蛹”。我相信“蛹”的能产和暗物质的不可穷尽。“深度形式”必然从内部诞生,“来自事物最内在的叫喊和欲望”。
我们的诗,不是修辞不够,我感觉修辞似乎表现过剩,动不动就堆砌,倒是深度非常欠缺。必须深,一深,再深……因为大雪还在加强,寒意还在加深……所以一首诗必须高度精警和最大程度地体现生命内部的“雪崩”(或生命事件),体现一种冰的火。一个诗人绝对不能任其大雪封“山”,任其笔管里充斥冰碴,绝不能把你的冷毫不负责地加诸比你更冷的人。你的笔管应该接通你的地火,把你炽烈的熔浆和你的最大的悲悯推进“橡皮管”,推进你的创造性的笔尖。
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最后的诗。每一次飞行都必须是极地飞行。每一次写作都必须把自己耗尽。
为啥“每一个克利都是不同的克利”(杜尚),为啥克利的画作随处都是“伸手可及的‘音乐’。它们动人心魄,却无从倾听……不可预期”(刘云卿),这里自有不为人知的成因。
诗歌的质量除了“深度”以外,其次它“是由速度和果断性决定的”。(希尼)
而一个诗人的质量,在于他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简洁度。
诗歌是超音速的,也是超时代的。它的回音也许很远,远到我们无法估量。
我们的汉语是很具有能产性的,它很古老很悠久,它的黏土层很潮湿很神奇,可以“唤醒一种根源性的想象”,用它来创造一种“超音速”的、世界一流的诗歌是完全可以的。
诗集《猫的两个夜晚》序,黑丰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黑丰:诗人,后现代作家。主要著作有诗集《灰烬之上》《猫的两个夜晚》《时间深轧》,实验小说集《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随笔集《一切的底部》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于海外。曾获得罗马尼亚雅西第六届国际诗歌节“历史首都诗人奖”,纽约法拉盛国际诗歌节汉诗英译奖等。中南财大和长江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诗坛》编辑。
黑丰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