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希望青年科学家的研究能回答临床问题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文、图
基础科学家的研究让临床的医生在应对病毒时有了后盾,“希望未来的基础科学家能够回答临床问题,而不仅仅只关注SCI论文。”6月23日下午,在上海市科协指导下,由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等主办的市科协青年科技论坛暨“First Talk”青年讲坛“从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到新发再发传染病的防治”研讨会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这样表示。
谈病毒
病毒传播一定是有极限的
“在病毒面前,临床医生一直是被‘吊打’的。”论坛中,当被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姜世勃丢过来有关“二阳”的问题时,张文宏这样笑言。
他表示,每一次新的传染病的到来,都是对科学家的一个拷问:科学家是不是做好准备了?而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一直是时刻准备着的。“因为每一次新的病毒一来,我们手头可能还没有诊断试剂,对疾病也还不认识,但是你就得往前走。“我们临床一直在等着科学的救援能够赶快来。”
当然,当基础科学研究帮助解决一个临床一个问题,新的临床问题可能会马上出现。在面对新冠病毒时,初阳和二阳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亟待回答的新问题。
张文宏表示,目前在临床中,已经开始进行观察,并发现了一个现象:“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的突变一直没有突破奥密克戎家族,从我们临床对疾病的理解,我们感觉到它的进化开始到了一定的极限。病毒要突破也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它会有传播的一个天花板。”张文宏表示,如果再突破,就会开始违反生物学的一个规律了,“因为碳基生命的病毒传播,一定是有极限的。”
谈二阳
判断依据源于与基础科学的深入合作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非常好的就是,新冠病毒的突变始终在奥密克戎家族里面,那我们原来的疫苗、我们以往的感染就会有一定的作用。”张文宏表示,这也是在去年年底一波大流行时,他提出过的:去年这一波过来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正基于的奥密克戎病毒很难再被突破的考虑。“你只要在奥密克戎家族里面,我们就有交叉免疫。”
同时,对于今年5、6月份会有第二次流行的判断,则是基于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家的广泛合作。“第一,交叉免疫始终存在。第二,抗体是要衰减的,一般在4-6个月,当免疫屏障降低后,周边感染的人也会慢慢出来,但这一波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感染的人。”
同时,通过研究发现了因为记忆细胞的存在,可以在长达一年时间,保持很大的一个克隆,那么即使抗体很低了,无法阻止感染,但记忆细胞会让人有足够的能力,使得感染程度不像第一次时那么重。“所以我们会说二阳不是那么重,这背后是我们临床的团队和基础科学家非常深入的一个合作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他也同时认为临床科普要基于与基础科学的深入合作,而一旦有了科研的数据,回答问题就会变得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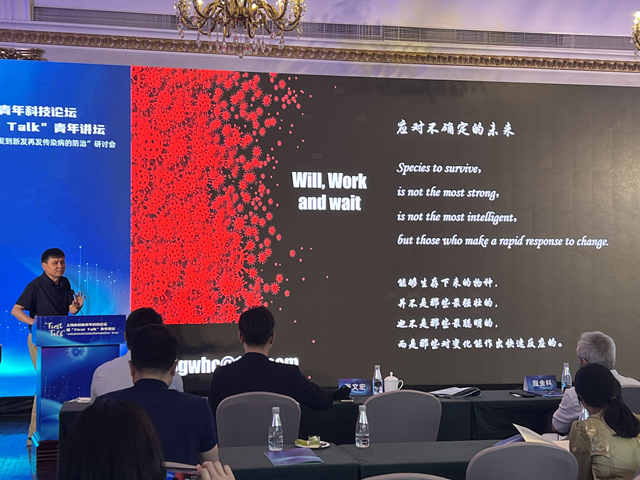
谈科学态度
希望青年科学家能回答临床问题
当天的论坛上,一批青年科学家就新冠病毒的科研成果作了专题报告,而张文宏则在主旨报告中直率地表示:“今天青年科学家展现了不少发表的论文成果,我觉得特别好,不过我也有一个呼吁,希望未来的基础科学家能够更好地回答临床问题,而不是将目标都投向SCI论文。”
“我们在端午假期里举办的论坛,当然不只是为讨论一个或几个论文在内容,我们更应该讨论大科学。”张文宏表示。“今天真正要讨论的是新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面对不停变异的病毒,或是未来新的病毒,我们科学家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张文宏表示,这一波大流行结束了,如果遇到传播很快而毒性又很强的病毒时,是否能够不要让临床医生“裸奔”。“在环境中病毒一直存在,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去应对?”
谁都不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更应该时刻做好准备。张文宏也将达尔文提到的三个W送给青年科学家:Will、Work、Wait。他建议在座的科研工作者,不要急于跟着热点去追踪。“自己擅长什么,往’死’里做,把这个领域做成第一流的,而不要人云亦云。”他表示,年轻人做科学,首先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喜欢,第二个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工作,然后就开始等待,因为在持续工作中,很多发现可能就是在不经意中诞生的。“你要的一切可能都会来。”
但等待不是守株待兔。“时代变了,今天不是说像爱因斯坦一样坐在伯尔尼专利局,问着自己窗外的那堵墙,就能想出来一个相对论,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期待今天在这里的所有基础科学家将来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现场,他更是将自己的邮箱直接亮了出来。作为临床医学工作者,他言明了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和更多的科学家合作。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文、图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