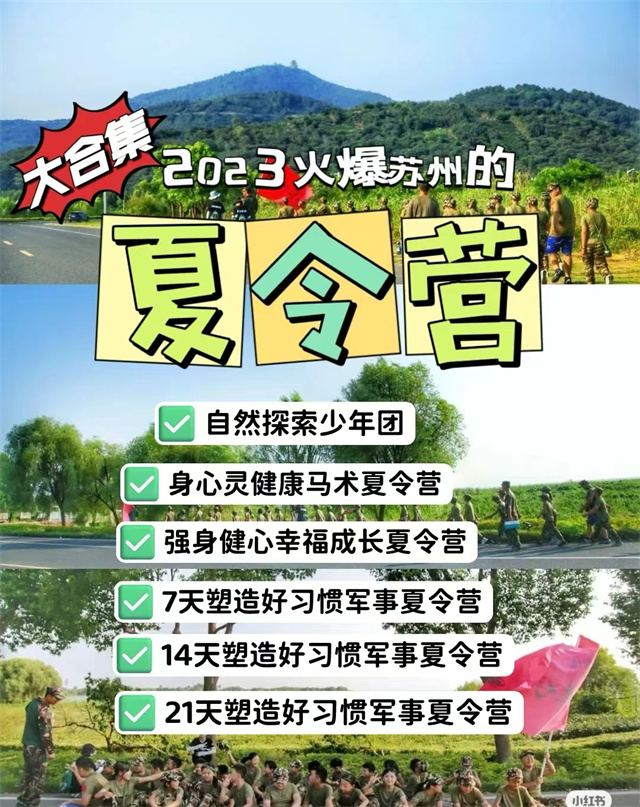小说人物塑造的力学原理

□黄梵
讲完小说的整体框架结构,我们来聚焦人物的行动,看人物行动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还是回到穿甲模型,导弹穿甲的时候,导弹与钢板的较量,必会给导弹施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力是导弹的喷气推力,相当于促使人物行动的推动力,反作用力是钢板阻止导弹前进的阻力,来自阻挡人物行动的困难。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构成对立,是一个对子,会同时施加到人物身上,这是小说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的核心。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发现不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者说发现不了加诸在人物身上的对立力量,这篇作品就很成问题。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说对立,不仅存在于文学,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所有文化。你在文化的任何领域,都能找到对立,原因就在,对立来自人性深处的悖论。人天然有追求安全与冒险的双重本能,这是令人性充满悖论的原因。比方说,落实到希腊雕塑,你会发现,人性悖论演化成了对立平衡原则。你看,希腊的雕像《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肩高的一侧,就追求胯低,肩低的一侧,就追求胯高,腿用劲的一侧,手臂就放松,腿放松的一侧,手臂就用力。希腊人通过摸索发现,人体姿态只要遵循对立平衡原则,视觉上会给人完美之感,就让人本能地喜爱。对立在古希腊雕塑中,比比皆是。
我讲诗歌时,曾谈到所谓的辩证法,说人根性上是携带着辩证法的动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对立又统一。既然人摆脱不掉辩证法,那么人创造的文化包括文学,同样也摆脱不掉辩证法。希腊雕塑的对立平衡原则,还可以叫对立统一原则,人体姿势不光追求对立,还追求这些对立的整体平衡,就是整体上还追求和谐统一。辩证法揭示了人的真相:人会把他本能中的悖论,投射到他创造的文化中,包括审美中。辩证法不让你的认识,滞留于事物的某一面,它总让你看到另一面,这会给你带来超越的视角,超越国家、团体的一己视角,拥有一双真正的人类之眼,让你真正看得清,想得透,说得好!
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说对立来自人性,你写的作品里,若不包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说对立,你也不要写了,因为你的作品不符合人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写那种,自始至终都是幸福和谐的小说? 就因为它不包含对立,违逆了人性深处的悖论。歌德对此人性,早有深刻的洞察:“世界上事事都可以担受得起/除却接连不断的美好的时日。”(歌德《格言诗二十六首》)。歌德是说,生命最不能承受的,是延绵不绝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意味着一成不变,不再有新鲜感。比如,普通人把长寿视为美好,设想一下,如果长寿的美好能延绵不绝,人可以永生,那么任何再有趣的事,是不是都会被永生化为无趣? 甚至可怕? 事情再有趣,也经不住时间的长久消磨。所以,我们人生的有趣或精彩,恰恰来自人不能永生,短暂使人生迸发出活力,精彩纷呈。日常生活中,人总期待变化,喜欢听到有戏剧性的消息,或巴望什么事有戏剧性的变化,所谓的戏剧性,它的根基还是对立。比如,人看足球赛时,一方面期待双方势均力敌,你争我抢踢得精彩,另一方面又期待一方能抓住另一方的差错,出人意料地实现突破。所谓的突破,就产生于原本势均力敌的双方,突然间出现了不平衡,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一时失衡,是导致戏剧性出现的原因。借用穿甲模型,当导弹还没穿透钢板时,作用力(推力)与反作用力(阻力),还彼此较量着,一旦成功穿过钢板,表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抗已经彻底失衡,反作用力突然消失了,事态就处于戏剧性变化的时刻。如果大家去看网剧,就会发现,网剧抓住观众注意力的法宝,就是戏剧性的剧情,他们称为翻转,每隔五分钟必会出现一次翻转。翻转既不能每时每刻出现,又不能相隔太长时间出现,拍网剧的人都知道,五分钟是最佳间隔。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彻底失衡时,翻转就会出现。翻转没有出现时,说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还在较量,还在胶着。有趣的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在小说中与在自然中,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作用力也就不会有反作用力。
作用力就是人物行动的推动力,它来自何处? 美国教创意写作的作家克利弗认为,激励人物行动的动力,来自人物的渴望。我部分认同克利弗的看法,他等于解释了导弹的推力,即认为作用力或说行动推动力的来源,是渴望。我认为,刑警在各种案件中寻找的动机,才是人行动的真正推动力,动机产生于人的需求。需求的轻重缓急可谓大相径庭,小到有人因妒忌,会拿钥匙尖,把别人的新车划出道儿,大到有人因贪财或仇恨,杀人越货等。需求与渴望是有所不同的,不是所有需求都达到了渴望的烈度。克利弗的渴望说,比较适合概括古典小说,在那里需求都变得比较极端,刻不容缓。根据我的写作和阅读经验,我在这里提出需求说。原本平衡的生活一旦出现不平衡,人就会产生试图恢复平衡的需求。比如,你一向衣着得体,可是有一天,你的衣服被勾破,得体的生活也就失衡,这时你就会产生想买新衣服的需求,以便恢复得体的生活。现代小说中的需求,不一定都很极端,有些需求远没有达到渴望的强度。比如,卡佛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导致他们行动的需求就比较轻微。卡佛在《取景框》中,让“我”产生的照相需求,既随机又轻微,只起到一时平衡心理的作用,远没有达到麦尔维尔《白鲸》中,亚哈复仇的需求烈度,没有达到试图永远平衡心理的长久作用。当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水里,他拼命挣扎的力量,才来自他脑中不想死的强烈渴望,这时的求生需求才有渴望的烈度。所以,把小说人物行动的推动力,即作用力的来源,归结为需求,这样既能概括古典小说,也能概括现代小说,概括小说中千奇百怪人物的,大大小小的行动。
回到穿甲模型,导弹靠推力飞行,代表人物被需求推动开始行动,穿甲时,出现阻挡穿甲的反作用力,就是物理学说的阻力,代表阻止人物行动的困难出现。这样就可以把人物行动遭遇到的困难,表述为是人物需求推动的人物行动,遭遇到了困难。
克利弗的渴望说,是让渴望不断受挫。我提出的需求说,与克利弗的规则类似,就是让人物的需求遭遇一系列的困难,令需求不断受挫。你会发现,古典小说为了让人物的性格典型化,作家会尽量让困难变大,因为他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才能让人的性格,显现得淋漓尽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也不总是有道理。比如,安娜卧轨赴死的行动,确实充分展现出她性格刚烈的一面,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她扑向车轮的刹那,行动中出现的躲闪和意识中的惊诧,却有违她的典型性格。说明什么? 说明人物深层意识导致的反常行动,并不符合通过激烈挑战,就能揭示典型性格的逻辑。安娜行动中的矛盾,实则预示了20世纪的小说人物,将部分脱离揭示典型性格的古典逻辑。
当然,你熟悉现代小说之前,还是应该先熟悉古典小说的做法。古典小说比较倾向同时加大需求和困难,把人物逼到墙角,使人物显现出典型性格。比如,你走在大街上,碰到一个魁梧的家伙,突然拿刀子对着你,你会怎么办? 你这时的需求当然是求生,需求达到了渴望的烈度,求生与有人对你动刀子构成了对立,对立的烈度会令你的性格显现出来。比如,有的人撒腿就跑,显现出胆小怕事的性格;有的人从兜里掏出刀子,显现出他也是硬汉的性格;有的人不逃,也没刀子可掏,只是用冷静的言语,设法让对方稍安勿躁,显现出冷静理智的性格。人物在小说中光有这些反应,还远远不够。吓得逃跑的人,如果真跑得没了踪影,动刀子的情节就白白设计了。就算跑,也要让他摔跤,或遇到路障、险情等,要让他的求生需求,遭遇一系列的困难。如果写硬汉掏出了刀子,就不能写成他一招制敌,瞬间就解决了问题,要像博尔赫斯写格斗那样,斗上好些回合,方见分晓。这样写才是小说,小说是过程的艺术,与诗歌是瞬间的艺术迥然有别。小说对重要的过程,不能敷衍了事,要用过程充分展示人物的需求,与行动时遭遇困难的艰辛对立。
我先举古典小说的例子,以美国19世纪小说大师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例。小说一开头,就给亚哈船长设置了需求:他有一条假腿,因为这条腿是被白鲸迪克咬掉的,他决心复仇。作家为了强化复仇的需求,让亚哈认为,白鲸迪克是故意找他茬儿,咬掉了他的一条腿。接下来,作家给复仇的需求,设置了大大小小诸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有二:一是先要找到白鲸迪克才能复仇,可是大海茫茫,到哪儿才能找到迪克呢? 二是就算历经艰辛找到了迪克,亚哈能战胜迪克吗? 小说结束时,找到白鲸的亚哈,并未真正战胜迪克,他和迪克打成了平手——同归于尽! 只有一个船员活着回来,讲出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麦尔维尔作为故事的操盘手,是残忍的,如果不是为了留下一个亲历者,回来讲故事,他恐怕不会让任何船员活着回来。你看,古典小说倾向把需求和困难都推到极限,以激发人物采取惊心动魄的行动,令人物性格得到淋漓展现。
现代小说中,需求和困难当然不会消失,只是需求与困难较量时,烈度不总是那么高,有时甚至比较轻微。我以俄国作家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为例。小说开头,博士生文书的需求是下连队锻炼,他偏偏被派往哥萨克人组成的六师,师长提醒他,哥萨克人不喜欢知识分子,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文书当然会硬着头皮,不顾师长的提醒继续下连队,所有哥萨克人都不搭理他。他躺在草堆上,寻思着破解之道,最终对房东太太当胸打了一拳,并拔出军刀,劈死了院子里的鹅,恶声恶气地命令房东给他烤鹅。他表现得特别凶,有违作为知识分子的一贯做派,却是克服困难的破解之道,可以赢得哥萨克人的好感。文书顺利融入了哥萨克连队,小说开头的需求得到满足,按说小说到此可以结束了,但巴别尔让文书晚上睡觉时,内心遭遇到新的困难,他做了有违知识分子良心的事——打了房东太太,杀了鹅。面对内心遭遇的困难,巴别尔让文书在心里采取了行动——忏悔:“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这篇小说人物的需求和困难,都没有达到《白鲸》的烈度,文书想与人打成一片的需求,无法比拟亚哈复仇的烈度,文书被人疏远的困难,无法比拟亚哈遭受的生死之劫。
所以,需求对现代小说人物的意义就在,起因与行动的力度、大小,不一定成正比,不一定是大因大行动,小因小行动,完全可以错搭成,小因大行动,大因小行动等。古典小说《白鲸》和现代小说《我的第一只鹅》,两篇小说的结尾,都没有完全步出困境,同归于尽只能算部分克服困难,文书内心的忏悔表明,他克服内心困境的努力还在继续。
《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黄梵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5月出版。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出版《月亮已失眠》《浮色》《南京哀歌》《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用绳子弹奏》等。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新浪读书原创连载点击率超过300万,已成为书写知识分子的当代经典。
黄梵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