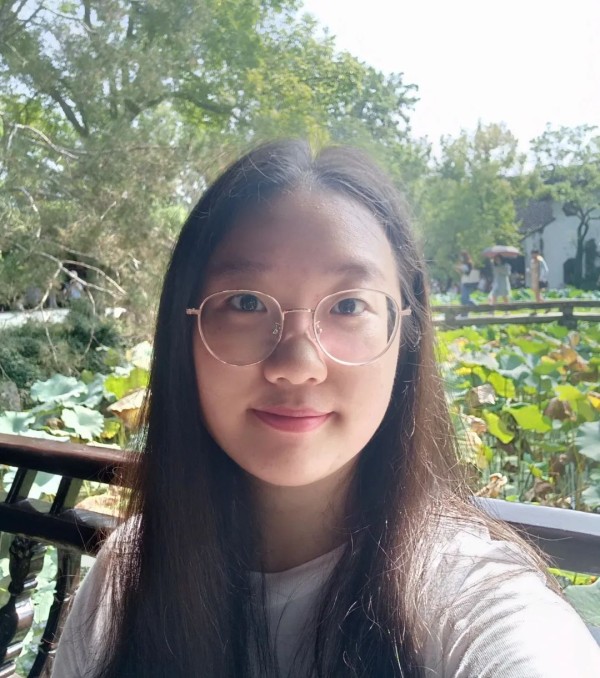荐读|恰如孤独,在他的花园里——读李郁葱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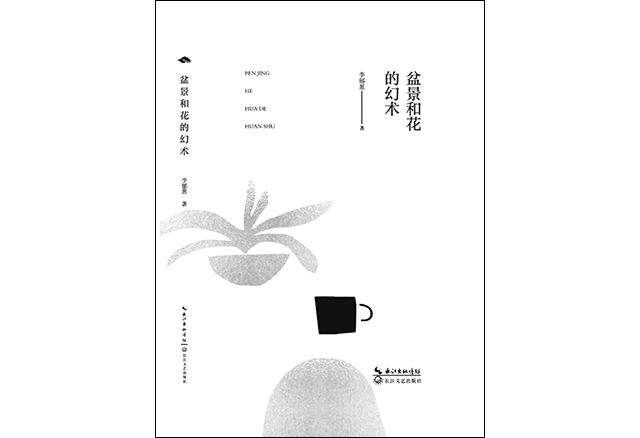
□周维强
从一个读者的视角来说,阅读李郁葱的诗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这里提及的“轻松”是相对于那些抒情性强、语词较明朗、词意较清浅的诗作而言,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诗歌美学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诗歌的认知还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于我个人而言,读李郁葱的诗,在不同的年龄段也能读出不一样的感知。当然,我所说的“感知”是相对的平衡,因为诗人自己也在解决自身的诗歌技巧和提升思想深度,而作为诗读者的我,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深度的积累,自然也会读到不一样的诗学意境。诗人在登高,作为诗读者的我也在攀爬。
就像眼前这本《盆景和花的幻术》,如果我在二十岁左右读到这本诗集,也许只读了一两首,就会把它摆放在书架的最高处,或直接束之高阁。不论是意象、技巧、氛围、语境,二十岁的我偏爱小清新、甜腻、口号甚至生活哲理式的短诗,而《盆景和花的幻术》显然是献给有一定美学基础抑或有一定沧桑阅历的诗读者的。
换句话说,诗人借助“诗”在寻找读者中的知己或者知音。
我和李郁葱2019年结识时,尚能从诗集《沙与树》中读到生态理念、天人合一的思考。此后,他在朋友圈所发的短诗,我都会第一时间去读,渐渐地,他在尝试诗歌技巧的多样探索,而我则从他的多样探索中,感受到一个不断行进的诗人在诗学道路上跋涉的孤独、忍耐和坚定探索的勇气。这个时候,对于他写下的一些句式抑或象征的隐喻,理解起来就有些难度了。好在一个诗人的思考有其生活的渊源,同处杭城,他的生活轨迹我亦曾到过,设身处地地思考,自然会明晰生活中所折射的悖论、复杂、歧义。一个没有诗学争议的诗人,显然不是一个大诗人。躬身于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中,我所见的,是一个忠诚于诗神而在真诚的诗心里生发智慧时,所表达的哲思乃至探寻生活真相时的虔诚之态。
比如《譬如草木》一诗,虽是“和唐晋兄庆根兄一日漫游后”所作,但这首诗中弥漫的冷峻气息依然有着一个人独舞的寂寥。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寄情于山水,是为了让山水的灵秀之气在体内酝酿出新的空间,滋养心灵。朋友相伴,草木春色,是为了缓解一种焦虑和困顿。草木隐藏于山石之中,恰如诗人隐于都市的人流之中。李郁葱诗歌中,有对古代诗人唱酬的隔空回应,这是一种神往。其实,古人远比我们逍遥,起码没有都市化生活带来的喧嚣与焦躁。好在有诗意的存在,可以破解焦躁带来的烦乱。
再如《和另一棵树》,这首诗虽然只有25行,但是却有着万字小说的内容体量。我在想,套用当今流行的一种写法,如果写同题我会如何去写。也许,我会从字面生发意象,顶多把人喻成树。而李郁葱在这首诗中,让修辞和想象力像两匹骏马一样,在稿纸上奔腾。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安下心来与自然交流的态度与修行,以物对应人的心境,在物我两忘的境界里,完成诗歌的写作。于树而言,孤独是一种常态;于人而言,何尝不是?尾句“是怎么样的人想成为另一棵?/但是的,我们还能够向下更深一点”,似乎有对自己诗学探究的一种自我鼓励抑或暗示,不只是诗学的探索,于生活的真相而言,多向前走一步,未尝不是一种境界。
在李郁葱诗歌的多样表达中,其诗境中的古典气韵一直是我要寻找的解读视角。诗人用不动声色的解构来完成自己诗学主张的写作实践。比如,对山水、人物、日常生活场景的古典折射,他像一个古代诗人行吟、思索一样,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想象力的欢愉和对日常事件的绵密情感切入。初看,其诗歌纹理中的复合质感,有其暗涌之流的紧促,待其细细去读,就会发现,以语言的多重参与,黏合词语的内在属性,得以从情理之中完成哲学与诗学的双重转换。比如《有所思》这首,以心灵之境对应生活之境,这类诗写有一特点,就是如何在其意象与修辞之中切入内心的真实感受。诗人已然将自己的诗心放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以高度抽象的诗性思维,化解“阴郁的江南”“鸟鸣”等意象,奇诡的想象力加持,通篇是一种埋伏在语言背后的思索。在汉语词意和古典意境的布局之中,我们看见诗人在语言才华上的表现,就是剔除那些惯用的陈旧词汇,代之以一些冷僻甚或孤绝的意境,完成心灵的复杂指摘。这是一种冒险,似乎,也是一种实验。
其实古人寄情于山水,在山水中不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也是一种美的质素的还原。李郁葱在另一首《遇见:一首练习曲》一诗中,与“蜻蜓”“云彩”“影子”的对话堪称复活了汉诗技巧的原始属性,打破僵化的语言结构,代之以个性声音的释放与语言模式的重构。我对这首诗的理解,就是用自己对汉语忠诚的勇气,来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意象进行价值上的重新定位和确认。诗人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自持与觉醒,利用常见的美学资源,完成独属于自己诗学属相的美学丈量。李郁葱诗歌给人的感觉就是陌生化、协调性,对一个意象进行语言表象和复杂本质的双重直言,须细细读,慢慢读,直到读到古典的核,读到汉语迸发的渴求,和内心的苦痛与隐忍重叠。
李郁葱的诗,吸引读者的,有多重镜面。尤其是在《盆景和花的幻术》一书中,所呈现的复杂戏剧化场景乃至词语大胆拆解时所惯用的个人情怀和终极表达,已然接近独特美学文本的二次贡献。相较于他之前诗集中异质性尚有隐藏的情形,在这本诗集里,诗人已然彻底摒弃了顾虑,变得有自己的专属美学区域的停留。年龄大了,关于诗歌的写作,有其格外较真的一面。
细细梳理,你会发现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中的诗歌,大都书写的是生活的日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思想的积累恰如屋檐落下的水滴,是一点一滴的渗透与沉浸。没有自说自话的空洞,没有人云亦云的口水,有的是消解生命无意的驳斥,有的是对汉语语境的拔高。在诗意的空间里,诗人完成了一种近乎朴拙的寻找,深厚的意蕴和诗意的建构里,是人性与美德双重闪耀时的惊喜。诗歌是一种美学,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是一种靠近,是一种和诗人诗心相互交流的过程。诗人有尊严,诗歌也有尊严,尊重诗人和诗人之诗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达成某种灵魂的沟通,而非其他。
比如《题花盆里的薄荷》这首诗,从诗题出发,诗人写的自然是生活的一个场景,一种植物,但是开头两句就会引发很多思考:“先得扎下根/哪怕是一小片的土地,让它有容身之地”,这,分明是自喻,写诗人在城市生活的一个理想。推而广之,是否也是一群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理想?扎下根,拥有容身之地。然后是静静地叙述,多种语境、多重语境里的解析与呈现,诗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他写薄荷颜色、气味,写薄荷的命运、生长史(当然,也是有隐喻和象征的意味),及至在尾节,一盆薄荷被困顿在斗室之中,是自我的选择?显然不是。如何突破束缚,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命题。让香气和绿意,濡染一下世界,似乎,也仅仅是一种安慰。这首诗歌中包藏着很多讯息,仔细去读,能够读出一层又一层的歧义,而这寻觅的歧义恰恰是读诗人的幸福。
而在《纪念:2016年3月16日》一诗里,写人间亲情,写母爱,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在真切隐喻和人心的靠近上有了完美的诠释。诗人用静气的词语,把自己复杂的心绪一再地浓缩。躲在暗处的,尚有可供心灵涤荡的斑驳。这首诗,其意象和涵义并不复杂,也并不难懂。词语的写意乃至情感的处理,都恰到好处。在生发性的表达上,冷静而沉着。四小节的叙述中,是情感上的一再递进,诗人是要把诗写进骨子里,写进纪念碑里,写进心灵的纪念册上,完成一种诗意的永恒重塑。“我偏爱于那孤独/是一座小小的屋宇”,这比喻,泪眼婆娑,生命的源头,一旦在人间断流,留给我们的,只有怀想,只有惆怅,只有孤独,然后躲在一个小房间里,暗自神伤。这小小的房间,留下了多少人间温情的故事。
而像《午夜的冥想》《如果那黄昏滑入悲哀》《房间里的眺望》等诗,以其冷峻、沉静、忧郁、慎思等情绪的传递,达成细致、敏感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了复杂、多变而让主客体共同延展诗歌美学的机敏、深邃的体验与感受。诗人以小博大,看似在路上,在陋室,在日常的生活空间里,实际上,其延伸的思考范围,并不比那些行吟四海的诗人视角要窄。这也是我常说的,诗人眼中看到的世界,和诗人心灵看到的世界,其比例并不相同的。心灵的世界可以丈量无限,以内心世界的坦露与复杂情绪的集结为特征,展示个性语言的情感传递,从本质上来说,是表达对灵魂,对精神超越,对时代性的介入与升华。
和诗人早期的诗歌相比,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中的诗歌,不论是在技巧、语言、意象的摘选还是氛围的营造,其诗写之路,要走得远得多。李郁葱的诗,总会给诗读者提供二次思考的空间,在读他的诗歌的过程中,我会情不自禁地顺着诗人的思路去思考,甚至有的时候,在其诗意的空间里,完成自己的诗歌写作。这也验证了诗歌写作的奥义,那就是还原生活的诗意。在坍塌的空间里建造丰沛情感的经验和诗意突破。
诗人奥顿有一段话,时常被引用:“在我看来,要成为大诗人,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中的三或四个才行: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
很多诗人和论者多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其实,我想说的是,创作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正如李郁葱在诗集里所说,需要阅读和忍耐。阅读好理解,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有表达的欲望。而“忍耐”却是生活的积累和天赋的折射乃至人格的准备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相信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会是李郁葱诗集里较为重要的一本,在这本诗集里,他已经把感性经验和理性判断用解构的方式,嵌入其中。一本诗集,就是一个花园。或者,就是一个家园。于诗人而言,在诗集里栖居,就是反省,就是凝思,就是在做着自我革新的修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属性。
诗集《盆景和花的幻术》,李郁葱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李郁葱:1971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浙江杭州。1990年前后开始创作,文字见于各类杂志;出版有诗集《此一时 彼一时》《浮世绘》《沙与树》《山水相对论》《盆景和花的幻术》等,散文集《盛夏的低语》《江南忆,最忆白乐天》《溪山无尽》《不须开口问迷楼》等。曾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诗歌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山花》文学奖、《安徽文学》年度诗歌奖、《北京文学》年度诗歌奖、李杜诗歌奖等。
周维强:从事评论写作多年,在《星星诗刊·诗歌理论》《青春·中国作家研究》《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数百篇。
周维强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