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他本质上是个诗人——我印象中的木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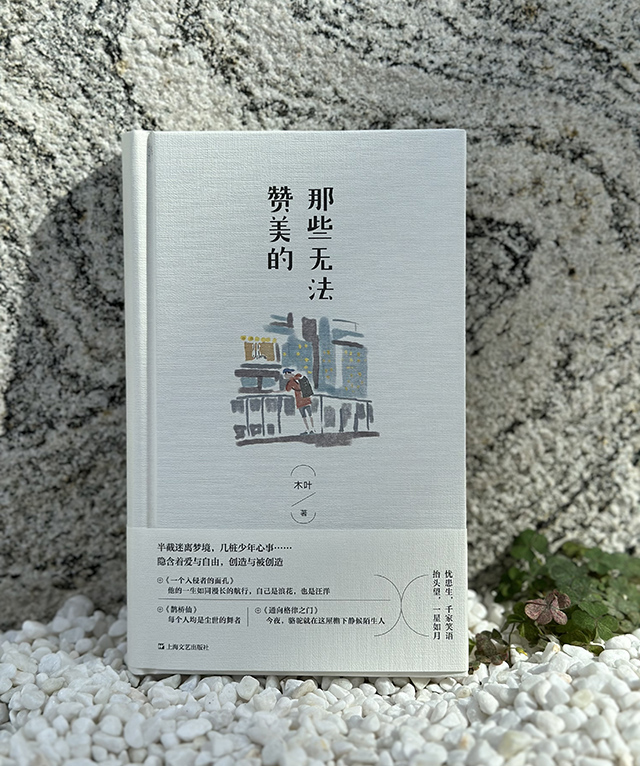
□兴安
认识木叶时间不久,尽管他是北京人,但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他在上海,一个北京人能够在上海文学圈开拓一片天地,并获得认可,不容易。
接触木叶是因为2021年的一次作家书画展,即第二届“梦笔生花:当代语境中的文人艺术”。主办方希望由我策展,于是我找到好友、作家孙甘露,请他推荐几个能书会画的上海年轻作家。他第一个推荐了木叶。之前我是知道他的,上海这十年里冒出了一批年轻评论家,张定浩、黄德海、项静、金理、黄平、来颖燕、龙其林,还有木叶等,他们都是70后、80后的青年才俊,这些新一拨的评论家是陈思和、程德培、吴亮、蔡翔、郜元宝、张新颖、葛红兵等50后、60后上海批评家的延续,也是文学批评代际交替的一个必然。
不久,木叶寄来了他创作的两幅书法作品,是草书,近乎行草,一看果然是练过的人。这几年,作家里写字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多数是由钢笔字直接转换为毛笔字,缺失了临帖的最基本的环节。中国书画是讲究传承的,尤其是书法,没有临帖的过程和工夫,很难进步,更难成形。木叶的字是经过训练的,也是有童子功的,他给我讲过他上小学时的故事:大约是三年级的时候,上书法描红课,有一个同学字写得特别好,在他的心目中甚至比老师写得还好,可奇怪的是老师却不知什么原因从不表扬他,但他在同学中非常受欢迎,大家都爱看他写字,也愿意和他交往,由于写字,他成了班里别具特色的人。由此木叶明白一个道理,原来一些像写字这样看似枯燥的事当你真能做到极致时也是会发光的。无论是出于小孩子的虚荣心也好,或者是荣誉感也罢,这种本能的对书法神奇功效的认识,成了他之后喜欢书法,并且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动力。我是相信这种原动力的,就像我小学和中学时,喜欢画画,并且包揽了全校每个班黑板报,而且还执着地参加各种作文大赛,并得了《北京日报》《中学生》杂志(可惜这个杂志,已经停刊很多年)全国征文的二等奖,我做这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让周围的同学羡慕,尤其是为了引起自己喜欢的某个女同学的注意。
那届“梦笔生花”展名家荟萃,大咖云集,有刘恒、邹静之、白描、西川、欧阳江河、张大春、蒋勋、南帆、杨争光、宁肯、徐则臣、王祥夫、荆歌、车前子、谢有顺、汪惠仁、葛水平、关仁山、张瑞田等等,其中木叶是最年轻的,那时他在北京的文学界和作家书画圈里还不太被人所知,但我坚持让他参展,并最终得到了组委会的认可。展览在北京琉璃厂的杏坛美术馆举办,很成功,由此我与木叶也成了朋友,但我们一直没有见面。
去年十一月,我与《草原》杂志的主编阿霞以及筱雅、蒋雨含等人去上海调研,朋友设宴为我们接风,我想到了他。但是我有些顾虑,当晚吃饭,下午才通知人家,是否有些失礼?但我确实想见见这位年岁比我整整小一轮的年轻人,手指不由自主地点发了微信,没想到他马上回复,说傍晚接完孩子放学就赶过来。晚上六点半我们准备开席,却未见他的踪影。我给他发了个微信,问到哪了。他回复:你们先吃,我还在送孩子回家的路上。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酒过几巡,都有些微醺了,他还没有到。有人提醒我,他肯定不来了。我辩解道,人家没说不来呀?有人说,那是客套。我不信,但心里开始打鼓。我有些黯然,独自举杯闷了一口酒。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沉甸甸的挎包走进来,嘴里不住地说“抱歉抱歉”。大家一阵惊呼,是木叶。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然后坐定。我问他吃了吗?他说没有,送完孩子就立刻赶来了。
之后作家甫跃辉也到了,他是因为给华东师大的学生上课,已经预先告知我们会晚到。就这样,酒局终于人员凑齐,一帮不是上海人的新上海人与内蒙古人在上海滩喝了一场大酒。
晚上十点多,酒足饭饱的我们又来到新天地继续喝,木叶坐在一旁,给我们每个人签名送书。那晚我们喝得挺晚,也畅快。其间,木叶对我说:兴安老师,我们其实很早前见过面的。我有些疑惑。他说,2001年,你给葛红兵出版了一本书《我的N种生活》,在复旦大学召开研讨会,我作为一家报社的记者参加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和您交流。我努力回想着二十年前的场景,却怎么也记不得了。是啊,二十多年了,我熟悉的那批评论家都老了,我也老了,连当年风华正茂、愤激犀利的葛红兵也老了。老了并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功成名就,“鸟尽弓藏”。我用“鸟尽弓藏”这个成语,只是取它的形意,我的意思是前辈们可以松口气,收一收架势,因为以木叶为代表的这批年轻评论家已经成熟了,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力了。新一代的作家需要新一代的批评家,他们应该是同步成长起来的,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
最近读了一些木叶的文章、诗歌以及他的新书《那些无法赞美的》,确实令我惊讶和佩服。他对路内、双雪涛、阿乙、鲁敏、笛安、冯唐、周嘉宁等年轻作家的论述,都给人新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感受。比如他评价安妮宝贝:“活得真已很不易,而她还活得那么认真。”而他对冯唐以及冯唐现象的批评,我觉得非常有勇气,也指涉得非常精准。最让我触动的是木叶的诗歌,我以为,木叶本质上是个诗人,即使是他的评论也浸润着诗性。我喜欢《妈妈在上海》这首诗:
妈妈将房间收拾得/就像自己从不曾来过//她登上东方明珠/说电视塔在晃,对面/大楼在晃,霾,也在晃//……在人民广场,在大光明影院/她想念家乡鸡飞狗跳的/菜园,还有麦地/牛羊低语,斑斓之蛇就位//……人生七十,越远的事越清晰/彼时,大人物都在,大事件不断/而今,她与卑微和解,不再畏惧/“死亡这个永无止境的故事”
最后,我以木叶的一段自述,作为我这篇印象的结尾:“终究,写作和批评都是始于局限和困惑,具具体体地从真实或虚构的生命出发,探讨并追索‘灵魂的深’,美的无远弗届,以及宇宙的未知未明。在这条路上走得远的人,可能无不保有一种创造性的爱,一种在光与暗之中不断升起的自由。”
兴安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