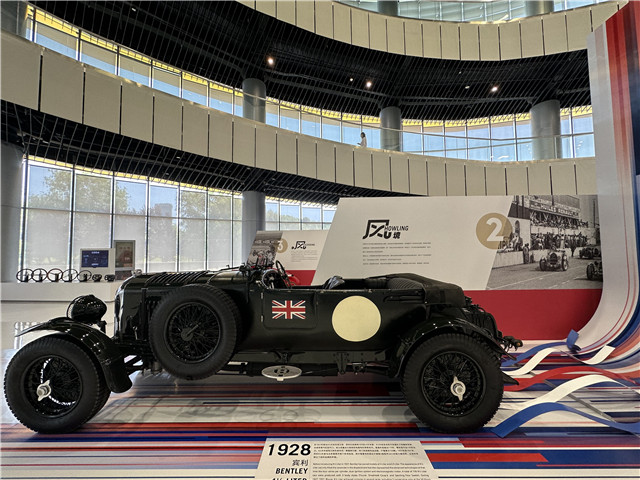又一意义重大的作品,在上海完成了中国内地首秀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提起被称为“法国当代作曲宗师”的迪蒂耶的大提琴协奏曲《遥远的世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总是赞不绝口,“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无论是于乐团、大提琴家还是作曲家,均是如此”。5月17日晚,作为上海交响乐团本乐季驻团艺术家、法国大提琴家戈蒂耶·卡普松,在著名指挥家叶咏诗的执棒下,献上了这部重要作品的中国内地首秀。
迪蒂耶是位公认的完美主义者,他只允许自己的一小部分作品出版,即便是《遥远的世界》这部让世人不断称颂作品也是一番自谦后的无心插柳。因为觉得难当重任,迪蒂耶退出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逝世100周年纪念音乐汇创作计划,但作曲家还是无法抵挡诗人的艺术感召,以《恶之花》中的《谜语》《凝视》《波涛》《镜子》和《赞歌》命名五个乐章,创作出这部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大提琴作品之一”的《遥远的世界》,更加自如地描述出了他想要的“一些更抽象、更纯粹的世界”。
刚接到余隆总监请他演奏该作的邀约时,卡普松是犹豫的,因为这部作品非常具有挑战性。虽然迪蒂耶在世时,两人经常合作这首协奏曲,“我还记得第一次演奏是在他90岁生日。”
但正是因为熟悉,才更珍惜每次演绎的完美,“他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我们一起工作了五、六年时间,直到几年前他去世。他事无巨细且非常挑剔,所以我坚信他写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想要的,他的色彩都是非常典型的迪蒂耶风格。”17日晚的音乐会上,他最终让上海观众领略了这种“迪蒂耶风格”。

卡普松和上交演奏家孙之阳
这部协奏曲的高难度,让不少人对今晚的演出备受期待。“拉协奏曲,独奏家通常会把乐队部分也背出来,但迪蒂耶这首根本没法去背,东一句、西一句,有点‘支离破碎’,拍点全打乱了,很难去找到古典音乐里一些‘格式化’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这样,但却是另外一种节奏。对乐队而言,也同样颇具挑战,因为大家可能都搞不清楚大提琴在拉些什么。这就非常考验指挥、乐队和独奏家三者间的默契,要像精密仪器般配合得当,携手去攻克演奏上的难点。”一位音乐学者在演出前如此说道。
第一次指挥《遥远的世界》,指挥家叶咏诗没少做功课。在独奏加入前,叶永诗就和乐队进行了好几天的排练。“我在熟读谱面细节的同时,也去听了不同大提琴演奏家的演奏录音,对比和总结其中困难的段落,以便在卡普松加入时多加注意。同时,作品里有很多换拍子的地方,我会数或者打分拍,先让乐队有个准备,技术的问题则需要大家自己去解决。”
令叶咏诗惊喜并松一口气的是,乐队成员们提前所做的充分练习发挥了作用,整个排练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是比较高效的一次排练,上交的乐队比我10年前来时更加成熟,对于一些新的作品或不熟悉的指挥风格,他们都掌握得非常快。”

卡普松和叶咏诗
这部作品与观众印象中的旋律性很强的大提琴协奏曲截然不同。从观众欣赏的角度出发,叶咏诗认为这样一首技术与审美门槛都较高的作品,需要聆听者带着“另一双耳朵”来发现配器中的精妙巧思,“比如打击乐器与竖琴、贝司等叠加产生的音效是全曲的亮点之一。”个中精妙只等观众一一挖掘。
除了挑战“硬骨头”,老朋友叶咏诗还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陈其钢《失乐园》、拉威尔《库普兰之墓》及《达夫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为沪上观众带来颇具法式风情的音乐之夜。
对上海来说,更多的重要作品选择在这座城市完成“首演”“首秀”,是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亚洲演艺之都对作品的吸引力使然,这里有上佳的舞台、完善的演出运行机制,能够让这些好作品有更好的承载平台。同时,上海观众的“懂经”,也让国内外的艺术家们更容易在这里找到知音,好作品和好观众在一个个美妙的演出中,完成了双向奔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