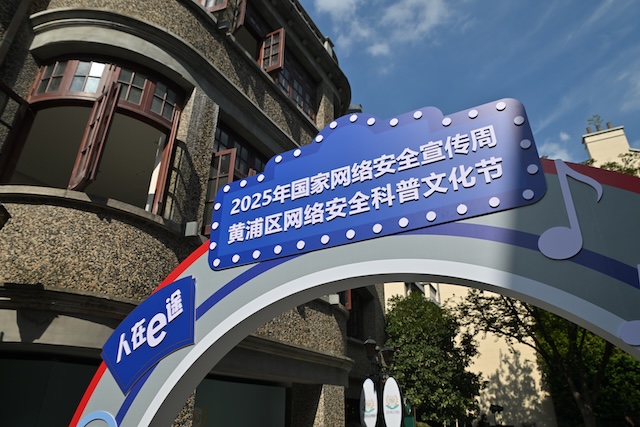从垃圾到艺术品,一场脑洞大开的美学实验

郑野许席地而坐变废为宝。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推开郑野许工作室的门,预想中无处落脚的“垃圾堆”并未出现。一条曲折却清晰的小径穿过各式旧物,蜿蜒至房间深处。那些已完成的作品仿佛隐匿在角落的精灵,悄然无声,却闪烁着再生的光芒。谈话间,手指不自觉拾起一根遗落的扭扭棒,随意弯折——仿佛思绪本身被捏成了具象的形状,不经意间,某个灵感的种子已悄然落地。
一把勺子,叩开创作之门
许多人从郑野许的作品中捕捉到一种童真气息,她并不否认。一件小巧的装置静静立在桌角:可爱的脸庞上,一颗剔透的“泪珠”正缓缓滑落。“我现在挺开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烦恼和崩溃的时刻。”她说,创作本就是诚实面对情绪之后的表达。

手工达人郑野许。
这份对情绪的坦诚,也延伸到她的创作媒介选择上。在成为旧物改造艺术家之前,郑野许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她的摄影作品常以冷色调与沉静气质示人,与如今色彩明媚、造型诙谐的装置仿佛出自两人之手。她认为,人有许多面向,充满童真的作品背后,并不必然是一个充满童真的创作者。所谓风格,不过是某一时刻的某种真实。郑野许坦言,快30岁的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绪体验是复杂的”。不过,“快乐”却是她一直在强调的字眼。放弃预设,抛开评判,“这时候你就是自由的,可以很轻松快乐地完成作品。”
郑野许从小就爱“胡思乱想”,家庭环境也影响着她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她的父亲是一名电焊工,弹弓、铁环等儿时玩具多出自他手。那些父亲焊接的小凳子,更是成了她的“画布”。她也不必担心自己搞的“小破坏”会惹来麻烦,动手能力极强的父亲总能搞定一切。

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工作坊。
如今在自己的工作坊里,郑野许也总是鼓励参与者大胆动手:“不要预判自己动手能力差或者没有创造力,一旦有了这样的预判,就很难真正去做了。”而最让她欣慰的是,原本只是陪同孩子的家长,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动手参与,一同感受创作的乐趣。
郑野许的创作始于2021年,因为一场朋友临时起意举办的生日聚会。来不及准备礼物的她便在办公室就地取材,用塑料勺子和吸管做成了一个小人。做得很随意,却意外受欢迎,“后来大家都想跟我交换礼物”。正是这一次的尝试,让她意识到旧物改造的过程是自由的,一切全在自己的掌控中。
“最初我就只是玩,‘垃圾’的时间、‘垃圾’的材料,做出来的东西也不追求有用或者美。”她笑着说。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带功利心的探索中,她走进了生活隐藏的走廊。那个勺子像一把钥匙,替郑野许打开了一扇未曾设想的大门,她甚至通过旧物改造赚到了钱。这件事的奇妙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生活中哪一件小事,会在日后成为命运的伏笔”。

孩子观看郑野许的作品。
与9000人坐满一个“体育馆”
郑野许几乎把自己称为“环保主义者”,她更愿意将创作定义为“快乐的分享”:“这是一个好时代,只要你认真做东西,就有机会被看到。”
她只在小红书上更新作品,目前有9000多个粉丝。若以流量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数据确实微不足道。“但你想象一下,9000多人几乎能坐满一个万人体育馆!”在她看来,这是一场值得珍惜的相遇。
她曾收到过一条几百字的私信,一名观众在广东广州参观了她的展览后写道:“展览上有一盏台灯,落在墙上的影子很温馨,我很喜欢那盏灯……在未来某个时刻或者我因生活压力焦虑不安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这个假期看到的这个展览,这是我今年的美好瞬间。”

郑野许工作室内陈列的作品。
这也延伸出她常思索的一个命题:让一万个人匆匆浏览,还是让一个人真正被触动?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那不是数字,而是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回响。
越来越多人开始为她寄来旧物。一位海南的幼儿园老师整理出几大箱淘汰玩具,细致地按颜色分类,自付运费寄到她的工作室。“大部分人对旧物的珍惜已经达成共识。”郑野许告诉记者,因为那不是垃圾,而是许多人共同珍视的回忆。通过郑野许的双手,这些旧物会改头换面,获得新的生命,并再一次走进许多人的记忆中。
起初,父母并不能理解,身为专职摄影师的女儿怎么就突然转行倒腾起“垃圾”来了?直到今年来上海,实地参观了女儿的工作室,他们的心结忽然就解开了——工作室里有一件卡通人物作品,它的“脑袋”是一盘废旧磁带。这盘磁带是多年前,父亲带着郑野许在老家一处待拆迁的老宅里捡到的——往昔的生活和亲情陪伴的记忆,此刻无比具体,又充满想象力。

用废旧磁带制作的卡通小人。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摄
郑野许至今保持着捡东西的习惯:日常收集瓶子、瓶盖;如有朋友搬家、参加活动时,她还会关注那些被弃置的物品。但她话锋一转:“该丢还得丢!”她并不赞成无节制地囤积,“不要想着某样东西日后可能有用,心态要放松一点,”经历过因囤积旧物而影响日常生活后,郑野许的话里带着一种释然的理性,“你不丢,它们将浪费你的时间、空间还有心情。”
有人质疑她在二手平台采购创作材料,这算不得真正的环保。她却很坦然:“环保和便捷的生活不应该是对抗关系。”换句话说,在她看来,环保不应是苦行,更不应该变成某种极端的抵制行为。普通人完全可以在便捷与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比如重复使用一个购物袋,比如给旧物第二次生命。
至于“环保主义者”这个标签,郑野许认为,大家认可她对于物品再利用的一些创意,那就很值得高兴。如果非要说这些作品带来了什么“意义”的话,那应该是,它们再次提醒人们:快乐可以很简单,创造也未必需要昂贵的门槛。
那些“无用”之事,照亮生活
那盏被观众牢牢记住的台灯,如今就在郑野许的工作室里。它创作于广东广州,没人能想到,它的雏形是一根从朋友那里拿来的弯管水龙头;它的底座原本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红色塑料凳——被网友调侃为“广东省凳”——被刷上银色涂料后重获新生;而其他材料则是各种捡来的废旧物。改造中最难的是拆解水龙头的接头,郑野许买了很多工具,一点点摸索,才把它切断。“去学习使用工具,然后最终达成自己的效果也是很好玩的。”她说。

用废旧弯管水龙头改造的台灯。
东拼西凑、随性而为,为什么却能创造出格外打动人心的作品?郑野许的回答出人意料:“最关键在于,我没有从工艺制作的角度去做这件事。”如果一开始就奔着“精致”去,或许根本就不会有这盏台灯的诞生。
她的工作坊不定期开展活动,由于尚无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所以无法提供标准化的材料包。所有材料都随机挑选自她的“收藏”。“每个人拿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展开联想。”她常以勺子举例:“它们可以裁剪成很多不同图形,要学会从别的视角去观察它,它已经不具备本来的实用意义,去仔细看它的颜色、形状、材质,包括感受它的触感。”比如剪去勺柄,它是一个圆润的脸;剖成两半,就是一对耳朵……所谓创造,就是跳出物品原有的设定,看见新的可能。
郑野许的创作心得是:尽量避免重复使用同一种方法,“一旦形成固定思维,创作就停止了”。

废弃物经过一番改造重获新生。
采访中,她不时说出一些让人怔住的句子。譬如被问“是否有过想放弃的时刻”,她答:“一切都太顺利了。”在她看来,社会总试图将每分每秒都标上价码——“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十句话概括一本书”……但她坚信,“人应当被允许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那不算浪费”。
或许,她的作品本身也注定是“无用”的。它们不解决什么实用需求,甚至不承诺永远存在——有些被拆解重组,有些最终仍回归“垃圾”的身份。但正是在这“无意义”的游戏中,郑野许找到了高度的自由:没有标准,没有成败,只有手指与材料之间的对话,以及心绪被捏成形的那一刻的快乐。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