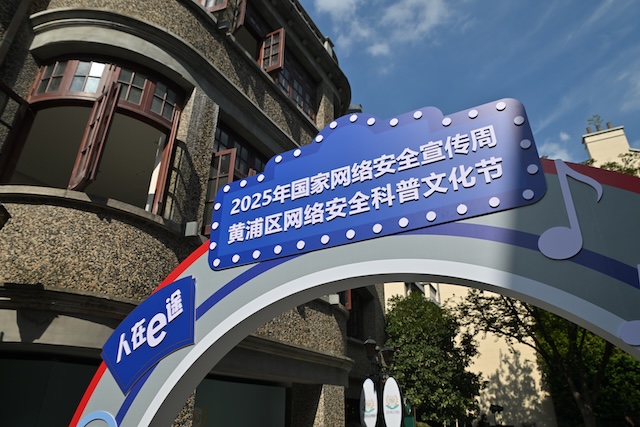叹为观“纸”:从絮渣到人类的精神史诗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新华社/图(除署名外)
一张薄薄的纸,为何会成为链接古今、沟通文明的重要载体?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洪雅在新作《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中,透过考古发现和史料辨析,揭示了纸张如何从不起眼的“絮渣”,发展成壮观的“纸世界”,进而走向全世界。这不仅是技术的演进,更是一部承载人类情感与信仰的精神史诗。
纸张原是丝织品?
1957年,一支施工队在陕西西安东郊灞桥镇砖瓦厂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西汉墓遗迹。经考古学家清理,铜剑、陶钫、铁灯、半两钱等文物相继出土。这些是西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不算稀奇,但考古学家的目光被一团“废麻絮”吸引了——那是压在一面铜镜下的纸状残片,层层叠起,有88片之多。
这些残片曾一度被鉴定为纸,并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所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因出土于灞桥,故称“灞桥纸”。由于考古学家将墓葬的年份定在西汉中期,这意味着灞桥纸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经问世,早于“蔡侯纸”。同样,20世纪70年代后期,甘肃居延出土了金关纸,陕西扶风出土了中颜纸,甘肃敦煌出土了马圈湾纸,经一些学者的检测和断代,它们也都早于“蔡侯纸”。
难道“蔡伦造纸”的传统叙事有误,造纸术的起源还得往前推?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关键在于如何定义“纸”以及如何确定这些出土物的年代。有学者认为,无论灞桥纸还是金关纸,上面都没有字迹。比如灞桥纸,就是包裹或衬垫铜镜用的。

赵洪雅(右二)拜访纸史研究专家李玉华(左二)和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忍之(左一),了解造纸工艺。受访者供图
不用来写字,那还能叫纸吗?不过,这可能是一种认知误区。“纸最初指的是丝质品。”赵洪雅介绍。东汉许慎编写《说文解字》,把“纸”解释为“絮一苫也”。原来,先民经常在水中漂洗击打丝絮和织物,并把在这一过程中附着到漂器上的絮渣晾成薄片,称其为“纸”。因此,纸最初的含义,其实指的是一种质地较差的丝质品,古籍和出土简牍中就有不少这类用法。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根据绞丝旁看出纸和丝质品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先民发现在漂洗时出现的絮渣成型后可以使用,而絮渣含有丝麻,这为造纸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启发。灞桥纸、金关纸等出土物仅就材质而言已经与后世的纸张非常接近,只不过因其初衷和工艺还不能用于书写而已。
“这提示我们:第一,不要从古书里一看到‘纸’字,就望文生义理解成今天的纸。第二,也不能因为古纸上没有字,就断定它不算纸。”赵洪雅说。保守地说,最迟至西汉中后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的雏形。到了东汉蔡伦的时代,植物纤维纸就跨入了新的纪元。
为什么蔡伦仍是“鼻祖”?
这是不是说,蔡伦造纸没那么重要了?当然不是。我们需要拉长视野,将造纸术的发明放置于“以纸代简”的漫长历程中,从而锚定其意义。
赵洪雅告诉记者,在纸张流行以前,中国古人常用的书写材料首推竹木简,就是把竹子或木头削成薄片,写上文字后按顺序编连,形成典册。相比于甲骨、石砖、金属,竹木简优势明显——原材料易获取,价格便宜,制作工艺简单,书写流畅,方便携带和保存。因此从先秦到两汉,竹木简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出土文献,如马王堆汉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都是竹木简。
纸的形态和作用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图为制伞师在为油纸伞上桐油。
竹木简之外还有帛书,其材质是由蚕丝制成的缣帛,因价格昂贵,只有权贵才用得起。比如马王堆汉墓的墓主辛追夫人,丈夫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堪称封疆大吏。考古学家在辛追夫人的墓中找到了《周易》《老子》等数十种古籍,皆为帛书。当然,这些书不一定是拿来看的,而是身份的象征。
竹木简和帛书的区别,类似现在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实际上以缣帛在古代的珍稀程度,将帛书定位为奢侈品或许更合适。而竹木简哪怕再平装,老百姓也难以使用。何况竹木简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积累多了以后极其沉重。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非常勤政,每天审阅的文件重达上百斤,得用车运。这对保存和查阅都是不利的。
这给纸张的崛起留出了空间。东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22岁的邓氏被汉和帝立为皇后。邓皇后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喜欢读书写字,且性格朴素,崇尚节俭。鉴于帛书太贵,竹木简又太重,她命宦官蔡伦设法改进。蔡伦在宫中侍奉二十余年,富有才学、做事认真,接到命令后,他在漂絮法的启发下反复实验、不断摸索,造出了“蔡侯纸”。
“蔡伦的贡献是创造性的。”赵洪雅说。首先,他在丝麻之外增加了树皮、破布、渔网,扩大了原材料的范围。其次,从前的雏形纸质地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蔡侯纸”则表面光滑,易于书写。可以想见,蔡伦必定升级了工艺,只可惜史书未载,后人已无法复原了。“最重要的是,因为蔡伦的改造,造纸业从纺织业独立出来,有了自身独有的制造目的和使用需求。”赵洪雅总结道。从这个角度将蔡伦定位为中国造纸业的鼻祖,属于实至名归。
纸扎技艺源远流长。图为一位匠人在制作花灯。
蔚为大观的“纸世界”
不过,“蔡侯纸”发明后并未马上取代竹木简,一统书写江湖,尤其是政府公文,仍然长期用竹木简。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要讲到汉朝的行政方式了。
汉朝可以说是“诏书治国”。皇帝口述诏命,御史大夫拟成诏书后发给丞相,丞相再下发给中央和各地方衙署。汉朝鼎盛时期有100多个郡、1500多个县,也就是说一份诏书在传达过程中将裂变成超过1600份,要是县继续往下发,数量就更多了。地方衙署隔三差五会收到诏令,于是保管成了问题。如果诏命写在竹木简上,那好办,把新简接续到旧简后面就行。可如果诏命写在纸上,东一张、西一张,该如何应对呢?竹木简能编连缀合,便于保管的特性,使其面对纸张的强力冲击,依然保有一席之地。
竹木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历经了从东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岁月,长达数百年之久。其间,人们“竹纸并用”,并且形成了某种分工——写普通的信件、书籍,主要用纸,包括账簿、户籍、名册在内的政府文件则多用竹木简。
然而纸张取代竹木简毕竟是大势所趋,加之南北朝时战乱频发,致使大量政府文件毁于战火,这给了纸张大规模普及的机会。至隋唐时期,纸已然坐稳了书写材料的“霸主”之位。造纸术也取得长足进步,出现了很多精品纸。唐代有工艺精湛的麻纸,皇帝制敕、官府藏书、佛经抄本等重要文献常用麻纸。起源于唐代、成熟于明代的宣纸,则是士大夫的首选。
唐宋之际,因原材料迭代、造纸产业集聚和造纸术的精进,纸张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其价格也大跳水。这促使纸张涌向“下沉市场”,不仅纸窗、纸帐、纸扇、纸牌、纸灯等成为日用品,图书也因成本下降而走入千家万户,甚至出现了纸钱、纸钞。“纸世界”蔚为大观。中国的造纸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等地,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游客挑选用宣纸制作的文创产品。
Qa 生活周刊×赵洪雅
古纸有“灵”,带我们走进祖先的信仰世界
Q:您是什么时候,因何种机缘对古纸感兴趣的?
A:我和古纸的缘分与两次“普查”相关,第一次是可移动文物普查。201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读研究生,正赶上国家文物局开展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便对我校博物馆新入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登记和编目。这是我第一次亲手触摸中国古纸。毕业后入职国家图书馆,领导看中了我曾经整理徽州文书、学习档案修复的经历,把我分配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我们部门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具体实施部门,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牵头对全国各系统、各地区的古籍存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为每一部古籍办理“身份证”。这样我有了更多机会学习和了解中国上千年历史进程中不同形制、不同年代的珍贵古籍及其纸质载体,甚至有机会体验原书,近距离观赏这些珍贵古籍。
这两次普查是文物系统和文化系统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普查,而我均有幸参与其中,很难说不是命运使然。这些经历也使我对中国古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天然的亲近感。
Q:从字里行间,确实能感受到您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情感。
A:我想这是因为与其他品类的文物相比,纸张作为文字载体和凭信物,它承载的历史信息密度更大,传递的人文情感也更浓烈。这些按着古人手印、画着古人花押的纸张仿佛能够把站在时间线两端的人链接起来,这是瓷片、玉石、青铜器等其他门类的文物所不能比拟的。就拿整理徽州文书来说,那是我第一次在情感上近距离触碰古人留下的语言和文字,这种感觉是无比动人和微妙的。文书里有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卖掉房产的李寡妇、为变废为宝而出租田内旱厕的王二郎,他们都是历史上寂寂无名又真实存在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痕迹就凭着一张张写有契约文字的纸质凭证而留存了数百年。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国图有一幅《资治通鉴》手稿,是司马光现存唯一一张手迹原本。这篇手稿虽然只有29行465个字,其中有不少涂抹之处,但是司马光亲笔书写,笔迹非常端正,毫不马虎,从中可以一窥这位伟大史学家著书治学的严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这篇草稿所用的纸是司马光利用朋友范纯仁写给自己和哥哥司马旦的一封信札,在稿本末尾,有四行字被笔墨涂抹,这四行字便是范纯仁信札的内容。此外,卷尾还有司马光手书的一封“谢人惠物状”。也就是说,这一张纸上写了三部分内容,即范纯仁信札、司马光谢状以及《资治通鉴》草稿,所以古人称这幅草稿为“幅纸三绝”。要知道,司马光在洛阳修史的物质条件是十分优渥的,即便如此,还要将一张纸反复使用,可见古人对纸张的珍视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赵洪雅 受访者供图
Q:读您的《叹为观纸》可以感到,您的目光不局限于书写用纸,而是涉及各种纸,而且深入到背后的文化心理。您对丧葬用纸的研究就很有意思。
A:从考古学和民俗学角度来说,历史上各种丧葬用纸所展现的功能性,可能远比今人想象的更多元、更复杂。我曾在徽州文书里找到一份有意思的“购房合同”,交易双方竟然都不是现世的活人——买房的“方母吴氏”,已经故去;卖方更玄幻,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天神东王公与西王母。这份房契不仅模仿现实世界中的契约文书,煞有其事地写明了标的物的位置、范围和价格,还在末尾申明:“倘若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奏到泰山门下、女(玉)青案前发落,恐口无凭,立此断骨出卖五彩三间灵屋契文存照。”可见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白纸黑字的纸质凭证即便拿到阴曹地府,也是可以作为法律凭证的。纸张因此也具有了某种沟通神凡的特性。
Q:相比古代西方的莎草纸、羊皮纸,中国的纸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传承上千年?
A:莎草纸和羊皮纸只是在物理上改变了纤维的原始形态,并没有使纤维产生复杂的化学变化,从这一角度而言,它们虽是书写载体,但并不是“纸”。莎草纸脆裂易折,羊皮纸价格昂贵,从质地和成本而言,也不可与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同日而语。这也是为何纸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脱颖而出,成为通用的书写载体的原因。
Q:请介绍一下古纸研究的现状。
A:随着出土古纸样本的增多、科学检验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外纸史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传统的史学、文献学和考古学基础上,新近研究又将古文字学、统计学乃至田野考察等科研方法融入其中,加之显微分析、纤维鉴别等技术手段的辅助,使20世纪纸史研究的视野显著拓展,并一定程度上革新了部分旧有的学术结论,学术气象随之焕然一新。我创作这本书时,在全面吸收既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新的科研论断呈现给读者。我还把一些考古发现的精彩故事融入其中,希望能在繁冗的“故纸堆”中,将最鲜亮、精彩和动人心弦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新华社/图(除署名外)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