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每个人都能抵达自己的“长安”

电影《长安的荔枝》剧照。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9月,迎来了新学年,畅销书作家马伯庸穿着一件深色T恤衫,出现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领变者论坛”的讲台上,开场第一句话就带着幽默:“我(以前)是上外管院的,咱们算是同行。”台下笑声响起。他接着纠正主持人的说法:“我不是上班之余才写作,我是上班的时候写。”在又一阵笑声中,马伯庸开始了“写作的力量:从职场到长安”的讲述。
不再打卡上班的马伯庸,笔下的故事依然与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安的荔枝》中运送荔枝的征途,《太白金星有点烦》中玄奘的西游取经路,《桃花源没事儿》中寻找“桃花源”的过程……都是职场的映照。如今的写作,是他每天4000字的“上班节奏”。他还专门租了一处工作室,保持固定通勤、准点上下班的仪式感。

当了十年职场人
马伯庸,这位以《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等作品闻名的畅销书作家,也曾当过十年上班族,他将这段职场经历视为自己创作的最大宝藏。
马伯庸的职场生涯始于施耐德电气。他是内蒙古赤峰人,却一点酒都喝不了,“喝酒和喝毒药差不多,除了死不了外,极其痛苦”。然而,公司分配给他的第一个岗位就是销售岗。这个开局堪称“天崩地裂”。有一次去山东见客户,对方倒满一杯白酒,马伯庸试图推辞:“我酒精过敏,沾沾嘴意思一下。”桌下的同事猛踹他一脚示意:该喝还是得喝。
刚毕业的年轻人不敢耽误公司大事,一咬牙一闭眼,一杯白酒下肚,直接滑到桌底。出乎意料的是,合同竟然签成了。客户说:“这小伙子虽然喝酒不行,人还怪实在的。”
因不胜酒力,马伯庸转岗了,业务能力仍不见起色。他自嘲是个“I人”,“看到不熟的客户就哆嗦”。转机出现在公司准备办内刊的时候。“这活谁也不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企业内刊没人看。”领导找来找去,发现这个业务不怎么样的小伙子“好像还挺喜欢写东西的”。
马伯庸接手后,另辟蹊径,挖掘公司历史中的趣闻轶事。他以“施耐德电气演绎”为题连载,结果,不仅同事争相传阅,连客户也主动来问:“下一期什么时候出?”
再后来,他的职位越来越特殊——专门给领导写演讲稿。这个职位使他在公司中处于一种超然地位,既升不了职,也没有竞争对手,还没人能替代他。
在这个过程中,马伯庸一直处于写作状态。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版税收入已经超过工资,就决定辞职了。

电影《长安的荔枝》海报。
真正的兴趣不需要“坚持”
把兴趣变成职业,是不是会成为另一种“灾难”?马伯庸的答案是:“真正的兴趣不需要‘坚持’,没人会说,自己每天‘坚持’打两小时游戏,每天‘坚持’看三部电影。因为那是爱好,是休闲。写作之于我,就是这样,是自然而然的事。”
“辞职第二天,我睡到十点起床,一拍大腿:早就该辞了!”他笑道。不过,散漫生活从来不是他的理想。马伯庸的写作状态更有规律了,他以4000字一天的“上班式写作”保持着“唯手熟尔”。
“每天6:30起床,跑步,吃早饭,送儿子上学;7:40准时到租的工作室写作;17:00结束回家。”马伯庸笑言,自己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室。那个地方离一所中学很近,他还能听到上课铃和下课铃。一听到下课铃,他就站起来活动腰椎颈椎,休息十分钟;上课铃一打就坐下写作。“他们做眼保健操我也跟着做,课间操我也跟着做。每周一升旗,我也伫立在窗前目视红旗升起。”
这种自律保证了创作的稳定输出,“当然不是写出4000字,而是写了4000字,中间删删改改可能没那么多,但这样的确保证了‘手热’。”马伯庸认识很多有写作天分的人,一旦一两年不写,第三年写出来的东西就很生涩。“写作和所有技能一样,需要持续训练。”事实上,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文字才能更通顺,辞藻才能更雅训,思想内涵也才能逐渐变深刻。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有一个鲜明特点——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在他看来,这可谓上班族思维的自然延伸。在读“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时,一般人关注杨贵妃吃没吃到荔枝,或对朝政的讽刺。但以一个上班族的思维,他脑海中立刻浮现的却是:如果我是负责运荔枝的人,该怎么弄?要争取多少预算?协调多少个部门?组织多少人?运荔枝路线怎么规划?怎么写可行性报告?如何跟领导汇报?《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诞生的。
他喜欢在历史约束中创作,视写历史小说为“戴着镣铐跳舞”。“很多人觉得限制太多,但我觉得这种挑战才有意思。如果你给我一个架空世界,没有任何限制,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想。”他说。
马伯庸也直言自己曾犯的错误:在《风起陇西》中让三国人物吃辣椒,后来才知道辣椒明代才传入中国。“真实世界给我们限制——无论是器物、社会规则,还是历史事实,你能够巧妙处理好,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你写的故事在历史上没有发生,但能和历史上的每个节点都严丝合缝地对上。甚至有读者问:‘你这个是真的吗?我觉得和历史贴得上,但我找不到任何资料。’这个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
在众多作品中,马伯庸最钟爱的,是被他称为“写给学术界的情书”的《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非虚构作品正源自他大量阅读学术论文的爱好。

马伯庸分享职场与写作经历。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AI时代的写作手艺人
谈到这个时代AI对写作的影响,马伯庸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DeepSeek问世后,他和前同事、专业编辑三人同时用AI创作小说,看谁写得好。
前同事提出的要求是:“请写一个扣人心弦精彩万分的小说。”结果AI转了半天,输出一团糟。因为他的需求太抽象了。马伯庸自己输入了详细提纲:“以敦煌壁画为主题,主角是当地小混混和北大历史教授,教授发现外国人要偷国宝,小混混一开始帮外国人后来醒悟……”结果,AI输出的虽不能说经典,但也算是篇完整的小说。最终胜出的还是专业编辑。马伯庸说,编辑可能自己不会写,但会挑毛病——“开头不够深入”“人物不够立体”“这段需详细展开”,结果,AI任劳任怨地修改,最终成品堪为最佳。
“这个时代的专业能力,不是会用什么工具,而是能提出什么好问题。”马伯庸认为,尽管AI能够有效辅助写作,但它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尤其是在选题创意、提问和深度思考方面。
不过,马伯庸并不会用AI写作,“主要是因为AI写出来的东西不合我口味,修改需要大量时间,还不如自己写。”
他倒是对新生代作者有着一丝担忧:“我们已经出头的作者有个竞争优势——搜索权重。读者进书店看到‘马伯庸’,觉得他之前写得还可以,大差不差会合口味。但新人在没有与读者达成默契时,就要面临大量AI文本,很可能被淹没。”
他开玩笑地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写作者了。以后等我老了,就找个乌镇那样的古镇,做个小门面,放块牌子:手工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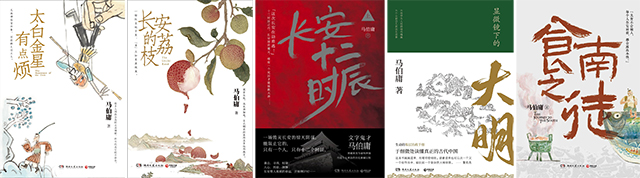
马伯庸在豆瓣上被读者收藏最多的五部作品。
每个普通人都有高光时刻
日常,马伯庸最喜欢观察小人物,因为他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高光之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在深圳签售时,图书馆不能卖书,只能签读者自带书。一个小姑娘因为爸爸忘了带书,当场哭了。爸爸跑出去买,满头大汗地空手回来——周围书店都卖光了。爸爸用哀求的语气说:“爸爸尽力了。”
作为一名孩子父亲,马伯庸听不得这种话,他叫来小姑娘:“第一,把你地址给我,我寄本书给你;第二,咱们合个影;第三,我跟爸爸也合个影——虽然没达成孩子心愿,但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后来,他得知,那位很胖的爸爸从未跑那么快过,“虽然是小事,但作为一个父亲,第一次为孩子燃烧自己到那种程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种日积月累的观察终会转化为创作素材。他最近的作品《桃花源没事儿》,书名饱含对现代打工人的共情:“什么时候你会说‘没事’?正是有事的时候。摔了一跤,别人来扶,你会说‘没事’;职场受挫,家人关心,你会说‘没事’。职场牛马需要这种韧劲。”
对于桃花源,他也有话要说,“我们还需要‘桃花源’——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终极矛盾之地、隐匿之所。现代人改变不了外界压力,但能改变内心能否迅速回血,减少内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逃遁之地,让自己休息一下,恢复内在的能量。”
马伯庸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情绪,但这种情绪实际上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回归职场,并不是说我们冷冰冰地把事情做完就可以了,职场上做事的背后还是要做人。不是说要追求八面玲珑,而是要始终善良。实际上,最终决定能在职场走多远的,还是真诚。
马伯庸认为,未来职场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并用它来面对挑战,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抵达的“长安”。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