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
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创造了现象级的文化IP。新华社 图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日前,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毓龙推出新作《花窗三十看“西游”》,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引领读者走进《西游记》的奇幻世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赵毓龙从文本源流、人物演变、跨文化基因等角度层层剖析这部作品的演变过程,并分享文学经典在当代的阅读与传承之道。
谈文本
西游是个滚过时空的雪球
青年报:您在《花窗三十看“西游”》里详细讲述了《西游记》的形成过程,能介绍一下吗?
赵毓龙:我们称《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就是有一个本事(原初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你添补一点、我增润一点、他组织一番,经过不同时代、地域的人加工,本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庞大的故事群落。《西游记》的本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在由玄奘口述、辩机记录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详细记述了求法经历,其中已经有一些看起来颇为奇幻的故事。
随着这些故事从佛教徒内部向世俗社会流传,人物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离奇。特别是宋元时期,市民文学发达,说唱艺人根据听众喜好不断添加和渲染,逐渐形成以斗法为焦点的西游故事。同时,戏曲里也有大量讲西游故事的作品。正是在这些悠久而丰富的艺术经验基础上,写定者加以整合、提炼、升华,编创出古代神魔小说的典范之作——百回本《西游记》。
青年报:为什么叫写定者而不是作者,《西游记》的写定者又是谁?
赵毓龙:我们一般将原创性文本的创作者称为作者,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像《西游记》这样经过不断“改写”的作品,完成其文本最终生产工作的人,还是称为“写定者”更合适一些。写定者整合故事形态和叙述经验,进行艺术提炼,完成“终极文本”。
《西游记》的写定者现在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并且作为文学常识进入了大众的知识结构。但在明清时期,你问一个人“《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是丘处机。历史上确实有本书叫《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西行到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经历,涉及沿途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及关防交通等。然而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人们把这部属于地理类文献的“西游记”跟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西游记》搞混了。
青年报:那吴承恩是什么时候浮出水面的?
赵毓龙:清代就有学者质疑了。比如纪晓岚指出,小说里出现了锦衣卫、司礼监等明代职官,而丘处机是金末元初人,因此《西游记》不可能是丘处机写的。但真正的“拐点”要到20世纪才出现。1922年鲁迅写信给胡适,提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他进行了详细论证。之后学界意见趋于一致,吴承恩最终取代了丘处机。
不过这依然不是定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据《淮安府志》记载,他的确写过一本《西游记》,但究竟是百回本《西游记》,还是同名游记或地理类书,不好说。而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把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归在史部地理类的。当然,我个人是倾向于吴承恩的著作权的,我们也能从吴承恩身上找到蛛丝马迹。根据研究,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可能是赘婿,而百回本《西游记》对赘婿持宽容态度。更重要的是吴承恩天性好奇,对神怪故事特别感兴趣,加上科场失意、仕途遇挫,积攒了不少郁闷情绪,需要宣泄,写就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的杰作,也算水到渠成。但这些都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我们至今仍没有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写定者的直接证据,只能说他是最有可能的那一个。

赵毓龙
谈人物
跨越文化的猴王蜕变
青年报:不只文本,《西游记》中不少角色也是累积而成的,甚至有域外基因。
赵毓龙:是的,孙悟空就是个例子。中国古代的本土猴王,以福建的最为著名,而福建猴王形容凶恶,属于“恶相”。为什么呢?因为福建山多林密,人类开发土地,难免和猴子等动物发生矛盾,双方经常起冲突。久而久之,猴王率群猴破坏农田、劫掠妇女、散播瘟疫等传说开始盛行。出于敬畏心理,民众纷纷为猴王设祠立庙,敬献祭拜,以祈求平安。到元明时期,福建的猴王信仰已经很成熟了,不少地方管猴王叫齐天大圣或通天大圣,建了大圣庙。“大圣”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和瑜伽教有关。瑜伽教源于印度,唐代传入福建,逐渐与本土道教融合,成为一种民间宗教形态。瑜伽教把敬奉的神祇称作“大圣”,如雪山大圣、雄威大圣等,出于同样理由,猴王也被冠以“大圣”的名号。
早期的大圣仍然是“恶相”的,它又是如何变成“善相”的呢?这就要讲到孙悟空的域外基因了。据胡适、郑振铎等人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有一部分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在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聪明勇敢、善于变化的哈奴曼帮助罗摩打败魔王,解救悉多。《罗摩衍那》的故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哈奴曼与本土猴王融合,形成了百回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
青年报:除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取经路上的许许多多妖怪,也有域外元素。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不是比较特别的?
赵毓龙:确实比较特别。大多数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世代累积型作品,都是在中华文学地理版图上发展起来的,《西游记》则超出这个范畴,融合了大量域外元素。孙悟空就是中外两大类猴王相结合的产物。猪八戒的一部分原型也能够追溯到古印度教神祇摩利支天。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保持着很强的文化自信,能够把域外元素合理地转化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是最能体现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部古典叙事文学作品。
在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拍摄的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插画展。新华社 图
谈“二创”
改编无界限,但要好玩
青年报:《西游记》的生成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文本天然具有开放性,因此哪怕有了百回本,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二创”。时至今日,《西游记》依然是影视化的热门题材,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毓龙:所有文本都具有开放性,改编《红楼梦》的也不少,只是成功的不多。因为《红楼梦》属于原创作品,文本大于故事。换句话说,它是文本IP,重述门槛比较高,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改编的。而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故事大于文本,属于故事IP,开放性更强,重述门槛也低一些。虽然有写定本,但大众没有被写定本的主旨和情节束缚,于是出现了各种“二创”。
青年报:改编或“二创”有没有界限,毕竟我们总说经典不能“魔改”。
赵毓龙:故事IP跟文本IP不一样,没必要设界限。文本IP,比如《红楼梦》,它是有原作者的,更重要的是,凝定的文本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相对固定,地位也很高,甚至说具有一种崇高性,有一些“神圣不可侵犯”了。这样一来,改编者就不能偏离原著的情节和思想太远,不然就成了您所说的“魔改”。但《西游记》这样的故事IP,尽管凝定文本也取得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但它对于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人们主要喜欢的还是西游故事,各种“二创”也不过是在重述故事,无论哪种艺术形式,包括文学改写、影视化改编、游戏改编,以及网上各种短视频、表情包,只要动机是积极的,策略和手法被大众接受,都是可以的。比如孙悟空有个叫“烦死了”的表情包在网上非常流行,我觉得就挺好的。
青年报:以您个人趣味来讲,会更钟情于哪一类“二创”呢?
赵毓龙:我个人觉得当代的《西游记》改编只要做到三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很好了。第一条是有趣好玩。《西游记》原著首先是有趣好玩,今天的大众之所以喜欢《西游记》,也是因为有趣好玩,如果你做到了,我觉得就达到60分了。在此基础之上,把神魔鬼怪塑造得有人性,有人情味,可以打80分。如果还能表达一定的批判性和讽刺性,那就是90分了。我最近读了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这就是一部90分以上的小说,我是非常推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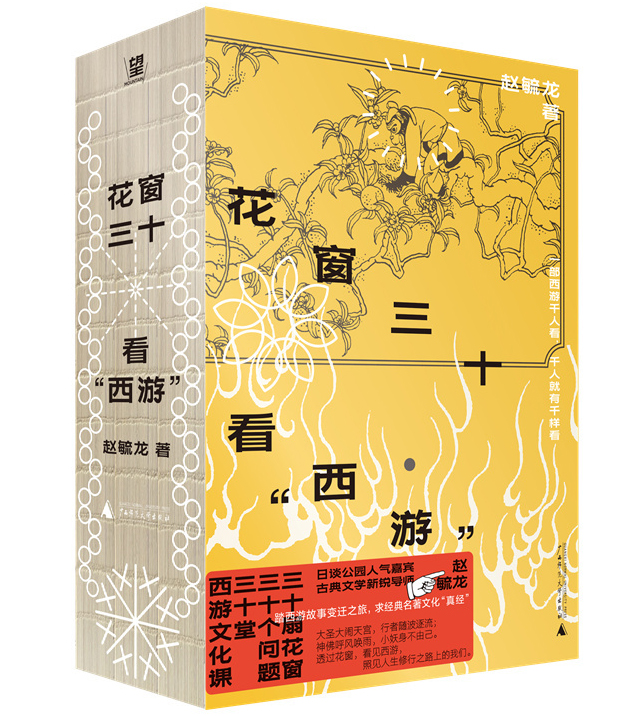
赵毓龙新作《花窗三十看“西游”》。
谈阅读
为什么仍要读原典?
青年报:既然《西游记》是世代累积而成的,又可以进行各种“二创”,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今天我们仍旧要读原典?
赵毓龙:首先,百回本《西游记》虽然不像《红楼梦》在文本上具有权威性,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足够的成熟度,思想上达到了足够的高度,作为文学经典,它本身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是需要被继承与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就是文学经典在当代阅读情境中的退场:一方面,当代文化有去中心化倾向,导致人们远离作为中心意义的锚定坐标的文学经典;另一方面,新媒介压缩了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来读写的时间和精力,大家不读书,都去刷手机了。
但正因如此,更要强调回归原著。因为如果脱离了读写、脱离了经典,我们在文化生活中获得的是什么?是情绪。短视频当然很有趣,我个人也看,但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满足,并没有在情感和思想上有所收获。而我们的人生要完整、文明要发展,除了情绪满足,情感和思想是更重要的方面,这需要通过阅读,尤其是阅读经典才能获得。
青年报:不过原著呈现的古代世界往往不那么美好,比如孙悟空和猪八戒长相丑陋凶恶,并不是影视剧里的可爱模样。《水浒传》里更是存在大量血腥暴力场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赵毓龙:所有的文学经典都具有时代性。一方面,它的生成与传播属于特定时代。小说家无论思想境界有多高,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输入到文本里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都具有时代性,不能用当下的标准去衡量。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又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书中许多观念和价值是超越时代的,为古往今来的人所共享,我们也因此与文学名著产生共鸣。我相信当代人读《水浒传》,不会因为看到李逵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就觉得这是一部好作品,而是因为它对现实的揭批、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且我们从小学习辩证法,很懂得在阅读过程中去粗取精,汲取真正的营养。总之我们要对文学经典本身有信心,也要对当代读者有信心。
青年报:我也认为应该读原典,哪怕读到血腥暴力的情节,也反映了古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古代社会本就不是田园牧歌。
赵毓龙:您说得非常对。中国古典小说像一道门,能带领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古人的心灵。当然,我们可以读历史文献,但当时绝大部分历史文献主要是由精英书写,精英很难关注到市民大众的生活,更不用说照顾到他们的心灵了,即便有所涉及,通常也戴着滤镜。中古以来的市民大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怎样的心灵世界,古典小说和戏曲是最好的门,推开它,我们能看到古人的渴望、向往和喜怒哀乐。古典小说也像一面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了古人的生活和心灵,反观自身,会发现有相通、相近之处。我们能在古典小说里看到自己。
青年报:最后,作为高校教师,能谈一谈您的学生吗?很多高校教师反映,今天哪怕是中文系的学生,读整本书好像都有困难,知识面也堪忧。
赵毓龙:这个问题有共性,大家普遍觉得即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阅读能力也在退化,对经典不感兴趣。这当然是一部分事实,但主要还是在以教师身份去“审视”学生,如果回归日常化的交际,我想说,我特别喜欢00后学生,因为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有青春朝气,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启发。我的学生经常和我分享新奇有趣的事,我手机里的表情包绝大多数都是学生提供的。他们的阅读能力看起来像是在退化,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阅读对象、媒介、场景、情态的转型,对于这些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转型现象,我们感到陌生,于是就觉得年轻人的阅读能力退化了。其实如果你真的跟他们交流,聆听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就会发现他们的阅读量也是很大的。他们经常向我推荐当代的优秀作品,比较时髦的作品,有的我完全没听过。在这方面是我追着他们跑。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年轻人贴标签。我们80后都被贴过标签,也一直在努力挣脱标签,现在我们进入到文化场中心,就不要给年轻人贴标签了。既然当初我们有自信,那么现在就应该对青年学生有信心。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