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古典滤镜,收获当下的“活人感”

刘奕新书首发现场。 青年报见习记者 孙思毓 摄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当前,喜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日渐增多,很多人在古代诗篇中映照自我,寻找情感共鸣。不过,古今之隔毕竟阻碍着我们深入认识与理解传统文化。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千百年前的诗词依然能拨动今人心弦,与我们隔空对话;另一方面,我们与古典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墙,难以真正进入。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奕则是一位“破壁人”。在新作《松声绿:乌尤庵说诗》中,他以诗学素养与个体经验为凭借,带领读者进入古典文本,探寻诗词里那股穿透时空依然奔涌的生命力。
古典诗词里,有我们的“蓝莲花”
生活周刊:我想从这本书的副标题“乌尤庵说诗”说起,乌尤是您家乡乐山的一座小山,也是您的自号,有意思的是,您管乌尤山叫“半成品”?
刘奕:对,因为它还有半步就要跨入名胜的时候停下了(笑)。中国的名胜有一个特点,它通常要靠人文加持,否则连风景都算不上,单纯是一个景观性的存在。比如,黄山成为名胜的时间其实很晚。明代有一些徽州文人特别喜欢黄山,不断宣扬,编纂了黄山的第一部志书,还有徐霞客、钱谦益等名人去游玩。于是黄山渐渐有了名气,成为“天下第一奇山”。
我家乡的乌尤山也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本名乌牛山,宋代诗人黄庭坚经过时改名“乌尤”,为什么要改?黄庭坚没有解释,但大家都接受了。除了黄庭坚,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李白、杜甫、岑参、苏东坡、陆游都经过或登临过此山。遗憾的是,他们要么没有留下作品,要么虽然有题咏,却并不出名,所以乌尤山始终没能跻身名胜之列,说起来是有些委屈的。

刘奕新作《松声绿:乌尤庵说诗》。
生活周刊:但乌尤山对您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刘奕:我喜欢乌尤山。一河之隔的凌云山是乐山大佛所在地,终日喧闹,而乌尤山侥幸保留了一丝清凉。乌尤山的风景也有独特之处。它远望峨眉山,近傍凌云山、马鞍山,中间地势平坦,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山下。登顶眺望,犹如一幅《千里江山图》于眼底徐徐展开,气象万千。我也喜欢爬峨眉山。四川云雾多,如果下过雨,或者是在秋天,峨眉山就非常静。
生活周刊:您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与这种对山水的爱有关联吗?因为很多古典诗词,都是文人墨客在流连山水时创作的。
刘奕:会有关联。小时候意识不到,等慢慢长大,尤其离开了家乡,感受越来越深刻。我本科和硕士是在山东大学读的,学的是古代汉语,博士考到复旦大学读古代文学,毕业后在上海大学教书,一直留在上海。上海是平地,我最大的苦恼就是没地方爬山(笑),这时候诗词里的山水就令我感到熟悉和亲切。
不止于此,当很多古典诗词重新浮现在脑海里时,我蓦然发现诗人写的那个景象、那份情感,我曾亲眼见过、感受过。可当我真的回到家乡——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只要有条件每年我都会回去——却又觉得那不是我记忆里的家乡了。对我来说,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理想的从前,就像许巍唱的,是永恒的蓝莲花。我回不去最初的故乡了,只能在诗词里寻找那朵“蓝莲花”。
生活周刊:我想,很多人都被古典诗词“戳中”过,您在课堂上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吗?
刘奕: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次讲阮籍的《咏怀诗》,讲到“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我解释说,阮籍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犯了选择性错误,那还可以改正、弥补,但如果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你无论怎么选都是错的,那才是真正的痛苦,一种无路可走的痛苦。讲到这里,一位同学悄然落泪了。那一刻,阮籍的失落与不甘,跨越一千七百多年时空,精准击中了一位现代年轻人的心灵。
生活周刊:这真是很神奇的事,古典诗词创作的时代距离我们其实很遥远了,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被它深深触动。这是为什么?
刘奕:我们常常讲现代跟古典之间存在断裂,这个话是不假,今天的生活方式跟古代差别非常大,但我始终觉得,技术的进步要远大于人类情感的变化。仔细想想,人类的情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生经验,古今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如果能突破古文的障碍进入到古典世界,我们会发现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人生遭际,古人的喜怒哀乐跟我们的喜怒哀乐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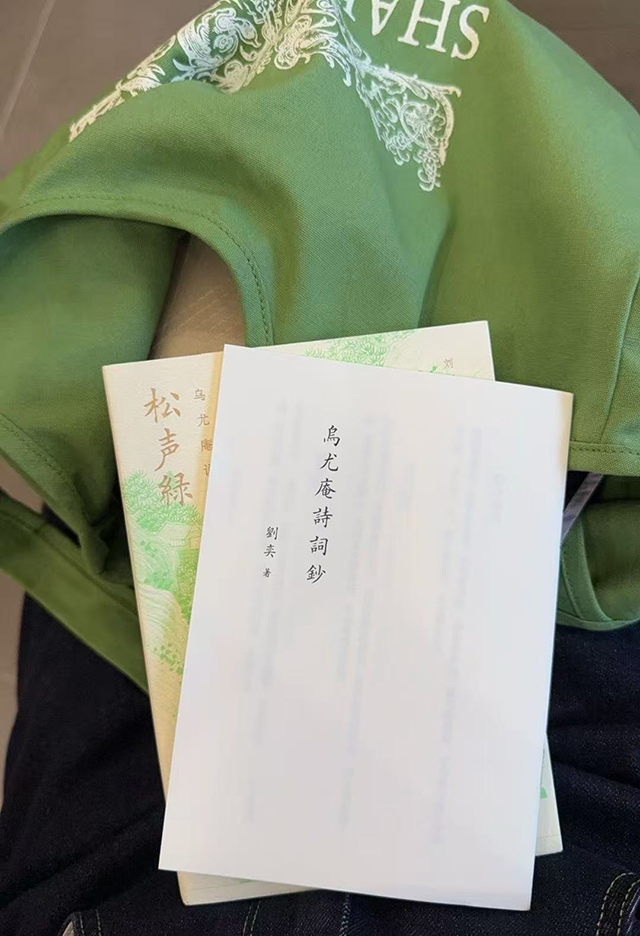
发挥生命的“元气”
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您推崇有力量感的诗词,为什么?
刘奕:我确实偏爱有力量感的诗词,看重有生命力的诗人。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人受到各方面的束缚,往往会感到压抑,但进行结构性改造又不现实,这时候就容易产生无力感。怎么办呢?必须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是一株草,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来。陶渊明和杜甫就是这样具有生命力的诗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极其旺盛的力量感,我非常喜欢。
生活周刊:但这两个人看起来风格迥异。
刘奕:生命力跟作品风格没什么关系,不是说豪放的就有生命力,温柔的就没有。在我看来,不论是婉约、精丽,豪迈、雄浑,还是自然、飘逸;不论诗人是在表达一己之悲欢,还是世间百态、历史哲思,只要有力量贯注其中,如同一口仙气吹给俑人,让本无生命之物活了起来,就都有生命力。
以杜甫为例。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年老多病,但他写“天地一沙鸥”“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乾坤、天地是无限的,在无限大面前,一沙鸥、一草亭、一腐儒都是非常渺小的存在。这是杜甫晚年心境的自况,他觉得很悲哀、很可怜。然而无论多么渺小,这间草亭、这只沙鸥、这个腐儒就伫立于天地间,不可抹杀。这是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哪怕落魄到那个程度,依然可以展现生命的力量,表示我不会屈服,我依然是我自己。
生活周刊:杜甫那强韧的生命力从何而来?毕竟从世俗眼光看,他过得挺惨的,一个现代人落到杜甫的境地,很可能会陷入沮丧走不出来。
刘奕:杜甫到死都过得很惨,看起来人生非常失败。但人生不是用得失成败衡量的,而是由你经历的一切、做过的一切、创造的一切决定的。杜甫在这一点上恰恰非常自信:就算我一辈子不得志,但我的诗歌会留存在历史长河中。我想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有这样的自信,而他们对生命力的发扬会影响到后人,促使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去对抗那种压抑和无力。
生活周刊:这是不是您在书里所说的“元气”?
刘奕:是的。元气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从文本层面讲的,诗歌的内在气息要贯通,好诗如雄鹰展翅,自有腾空之力,无须凭借外风。举个例子。在整理清代诗人王文治的诗文集时,我注意到王文治学习李白,写过一些歌行。当然王文治也很有才华,但他写歌行,往往控制不住,失掉平衡感。而你去读李白的歌行,比如《蜀道难》,既才华横溢,又恰到好处,长句和短句错落有致,永远不会失控。你不能不佩服他是个天才。元气的第二层更重要,是作者生命意志的灌注,作品里涌动着一股喷薄而出的热烈,让你觉得元气淋漓。李白、杜甫如此,年轻人喜欢的陶渊明、苏东坡也如此。
生活周刊:年轻人称之为“活人感”,觉得由此跟古人仿佛心灵相通了。
刘奕:古典诗词主要是士大夫创作的,他们欣赏美的东西。美就是没什么用,但能让生活有一点乐趣,让生命不至于那么干瘪。唐人去边塞游历,今天的人也会徒步旅行,宋人可以在一个房间里构造一片小宇宙,今天也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乐趣,这是相通的。
但要注意,我们对古典带有想象成分。比如我们游古镇,晚上街上都亮着灯笼。古代肯定不是那样的,因为蜡烛非常贵,通宵点太费钱了,只有逢年过节,像元宵节,有钱人家才会把灯笼挂出来,平常的夜晚哪里都是黑灯瞎火的。还有古人洗菜洗衣服,生活污水排到市镇的小河里去,水不知道多臭(笑)。其实诗词有过滤作用,把生活里过分浓郁的味道过滤掉,把美的东西留下。

当根脉相连,诗篇将彼此照亮
生活周刊:您在解读古典诗词时融入了很多个人的生命经验,使《松声绿:乌尤庵说诗》这本书跟充满考据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显得生动鲜活。
刘奕:我一直有种感觉,我们的文学史课堂离文学有点远。以我来说,刚毕业的时候,如果你拿来一首李白或杜甫的诗,我慑于威名,当然觉得那是好诗;但如果拿一首我不熟悉的诗,把作者名字蒙起来,问我这首诗好不好、好在哪里,我是说不出的,而且我也理解不了这首诗在表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教育让我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古典诗词,它们也不可能进入我的生命。所以我后来自己读书、做研究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理解作者是怎么构思、怎么表达情感的,有没有可能跟我产生呼应,进入我的生命。
生活周刊:您毕竟是科班出身,经过学术训练,而对非专业读者来说,一方面当然对诗词有兴趣,但同时又对文言文望而生畏。您觉得怎样入门呢?
刘奕:古典诗词最大的障碍就是表达,它的语言是古代的,有很多典故,修辞又很典雅。普通人最好找经典的、带注释的选本来入门,由此产生兴趣,打下一定的基础,再找自己最喜欢的诗人的全集,试着领会、把握。
选本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马茂元先生等人编过一本《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一本《唐诗选》。当时老先生都在,比如钱锺书先生就参与了很多工作。这两个选本在我看来是比较不错的。如果是讲解,我个人推崇顾随先生,他是叶嘉莹的老师,讲解诗歌结合人生、历史,有很多精彩的感发。另外上海有两位先生,刘衍文、刘永翔父子合著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从技术角度帮助我们理解诗词。可惜这本书绝版很久了,我非常希望能再版。
生活周刊:《古典文学鉴赏论》偏重讲创作的技术,这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门槛是不是有点高了?
刘奕:只要是艺术表达,就离不开技术,所以年轻人有必要对技术性的东西,比如格律、音韵进行一些了解。举个例子,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用上海话念一遍就知道,它押的是入声韵,但北方同学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有必要学一点技术,否则连古诗的押韵都搞不清楚。我一直强调,找到和自己意气相投的古诗,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需要知识体系支撑。这是必经的过程,要保持耐心。
不过也不要把读古诗词想得太严肃。我的看法是,如果有一首诗打动了你,一定是因为它触动了你生命中的某些经验,那就抓住它,从这首诗出发,慢慢建立和古诗词的联系。随着时间和知识的积累,一棵树会通过地下的根脉,与整片森林相连,不同的诗篇会彼此照亮。
生活周刊:根据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的研究,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都被后人改过了,而学者在努力恢复原貌。普通读者有没有必要去读原作,还是继续读流行版本就好了?
刘奕:我想还是应该根据学者的研究,尽量读原作,因为原作往往比改本更好。李白的《静夜思》,流行版本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原作是“举头望山月”。为什么山月要比明月好?我们知道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从小看的是山里的月亮,就是山月。不是随便什么月亮都能引起思乡之情的,海上生明月就不行,只有望见山月,李白才会想起故乡。
作者简介:
刘奕,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已出版《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等研究著作,并整理出版《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王文治诗文集》《秀岩集》等古籍。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