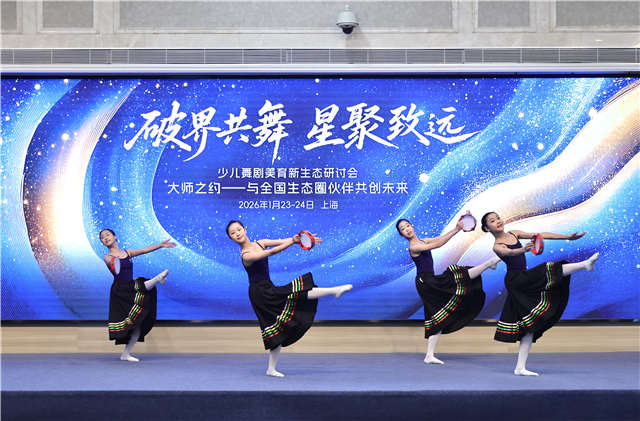当文学终于重新开始讲故事

战玉冰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近年来,悬疑推理类小说与影视作品持续受到公众关注,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重要类型。不过,针对其创作群体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战玉冰通过对法医秦明、马伯庸、陈思诚等一线创作者的访谈,梳理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的发展脉络与现状,解密了马伯庸、陈思诚等人的叙事技巧和类型化探索。他发现,风靡一时的“反叙事”倾向逐渐逆转,当代作家重新开始讲故事,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化出现融合趋势。而文学也由此在短剧的汹涌浪潮中,锚定自身的独特价值与坚守。
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
生活周刊: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悬疑推理类作品一直很火,不过聚焦创作者的研究不多,你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本访谈录的?
战玉冰:我之前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最近几年把研究范围延伸到了当代。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悬疑推理作家、作品数量非常多,类型也很多元,但还没有人做过系统梳理。我想再过20年,“当下”也就成为“历史”。我们作为今天的“在场者”,应该趁这些作家还在,一切经验和记忆也都还比较鲜活,抓紧进入现场,留下一手的口述材料。我第一批访谈了13个人,有写刑侦的法医秦明、写历史悬疑的马伯庸,还有几位小众赛道的本格作家,尽量囊括每一种风格。而且范围不局限于小说,游戏设计师吴非、话剧导演林奕、电影导演陈思诚也都是我的访谈对象。以后我还会将访谈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推理综艺的编剧、非虚构罪案类写作者等,预计是以三本书的体量,总计采访40人左右,力求覆盖当代中国悬疑推理类题材的各种面向和主要创作群体。
生活周刊:悬疑推理还可以细分出很多类型,比如历史派、社会派、本格派,哪一类更受欢迎?
战玉冰:历史悬疑和社会派推理的大众接受程度更高一些,这两类作品也比较适合影视改编。相对而言,中国的本格推理始终很小众。这或许是因为本格派以逻辑解谜为核心,非常硬核,读者市场比较受限。当然,反过来说,“本格谜”也因此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能并不那么多,但垂直程度却很高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比如推理小说主题书店“谜芸馆”主理人时晨、专攻密室推理小说的孙沁文等,都有着自己比较稳定和忠实的支持者群体。
生活周刊:访谈中好几位悬疑推理作家都提到自己是读福尔摩斯“入坑”的,看来这个IP影响是很大的。
战玉冰:是的,从1896年张坤德翻译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起,福尔摩斯就开始风靡大江南北,也涌现出不少效仿者。比如,1909年“南风亭长”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从它的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师福”,就是“师从福尔摩斯”;后来程小青更是塑造了“东方福尔摩斯”霍桑这一本土侦探形象,并且凭借“霍桑探案”系列小说,成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
20世纪中叶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曾沉寂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再度兴起;并且在新世纪以来,借助一波又一波的影视剧热潮不断收获新的读者。比如小罗伯特·唐尼和裘德·洛主演的系列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卷福”主演的英剧《神探夏洛克》等。这些作品引发粉丝创作了大量同人漫画、同人小说。在新的网络文化与粉丝文化语境下,诞生于139年前的福尔摩斯照样如鱼得水,展现出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唐朝诡事录》剧照。
生活周刊:悬疑推理小说为什么能持续发挥影响力,而《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却走向式微?
战玉冰:两者虽然题材相同,内核还是很不一样的。公案小说强调查案者的道德品质,只要他铁面无私,真相就能水落石出。《包公案》里的包大人甚至借助冤魂托梦或阴风指路来破案,查案的能力和技巧反倒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公案小说的目的是教化民众,通过渲染包大人料事如神、无案不破,提醒读者切勿作奸犯科。而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悬疑推理小说兴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逻辑推理既是人们的思维工具,也是休闲时的益智玩具,小说更关注查案者的智慧,强调运用推理破案。整体上来说,公案小说是一种前现代小说类型,侦探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类型,而中国历史上的这条“现代”的变更线大概就出现在清末,这也正是这两种小说彼此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公案小说就完全从历史上退场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拯、狄仁杰依旧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国民级IP。在新世纪,这些清官也借助侦探推理小说的改造而再度归来,比如《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一直到近年来特别火的《唐朝诡事录》等,都可以视为公案小说侦探化的类型融合结果。
马伯庸,类型小说的成功
生活周刊:进入本世纪,悬疑推理小说迎来了创作高峰,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法医秦明》似乎仍然在刑侦文学这条延长线上?
战玉冰:秦明和雷米都属于广义上的刑侦文学,但他们也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类小说进行了升级换代。比如雷米通过《心理罪》系列向中国读者和观众普及了犯罪心理学和心理画像技术,秦明更是将自己的小说和法医这个职业深度捆绑。但从他们的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出历史的延续,比如20世纪90年代海岩的作品着重塑造个人情感生活,推理味相对就比较弱。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形成了更成熟的都市受众,他们对专业化、职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医秦明的小说就呼应了这种趋势。

在《永不瞑目》和《法医秦明》系列、《心理罪》系列之间,折射出了巨大的时代变迁。
生活周刊:那么马伯庸这样的历史悬疑小说是如何兴起的?
战玉冰:这其实和2004年前后的“丹·布朗热”有关。那一年丹·布朗的历史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中译本出版,引起热潮。马伯庸、陈渐、冶文彪等作家受到启发,开始用类型小说讲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史上有取之不尽的故事资源,成熟的悬疑类型又保障了故事本身的可读性,这种写法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创作热潮。
而近两年,随着剧集《长安十二时辰》的“出圈”,古风悬疑影视剧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国产剧类型。刚才说的那几位作者,他们写于大约十年前的历史悬疑小说,最近两年都集中获得了影视改编的机会。
生活周刊:马伯庸的小说为什么好读,能戳中人心?
战玉冰:他很擅长从历史故事中挖掘出能和当代人产生共鸣的情绪点,比如《太白金星有点烦》讲述职场烦恼、《长安的荔枝》吐露打工人心声。而在具体讲故事时,他又能娴熟地运用类型小说的技巧,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描绘一幅准确、翔实的小说地图。比如《长安十二时辰》的情节都是在长安的坊市里展开的,《长安的荔枝》勾勒了荔枝物流图,《两京十五日》里则有漕运图。清晰的小说地图有助于在虚构的故事中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还能呈现出一条明确的人物动线,让读者更容易进入和把握故事。马伯庸的另一个秘诀是“倒计时”,让主人公必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抓住狼卫、保卫长安,在荔枝变质前将其从岭南送到长安,在十五天里从南京赶往北京……这保证了情节的紧凑性和紧张感。地图学、倒计时加职场共鸣点,在我看来是马伯庸历史悬疑小说成功的三大法宝。

《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倒计时”手法强化了情节的紧凑性和紧张感。图为剧集剧照。
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说,马伯庸的成功是类型小说的成功。
战玉冰: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大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包括严肃文学作家——借鉴悬疑推理类型,比如东西的《回响》、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生活周刊:你把双雪涛也归入悬疑推理作家吗?
战玉冰:你不觉得《平原上的摩西》是使用了悬疑小说的框架吗?其实欧洲早就有这种情况,埃科、帕慕克都曾经这么尝试过。而且悬疑推理这种形式是很适合探讨历史、人性等严肃议题的,以电视剧为例,前两年热播的《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在我看来都是套着悬疑剧外壳的年代剧。
走向悬疑,是为了找回读者
生活周刊:过去几十年,反叙事、反故事是创作的主流,但从你的观察看,现在似乎出现了向讲故事回归的倾向?
战玉冰: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于是有了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强化,先锋文学、私人写作随之兴起。这当然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走到极致以后,你会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几乎就不讲故事了,作者往往执着在某个情绪上不停地挣扎,而这种挣扎又无法让读者共情,导致文学和读者割裂、脱节,越来越自我封闭化。
问题在于,写作不可能仅仅面向自身,你的文本总要给人看,要产生交流互动吧?而现在的状况是,大众不关心文学,一部小说可能在圈内饱受好评,诸多奖项加身,但大众根本毫不关心,用王蒙的话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于是这两年文学开始“向外转”,严肃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悬疑推理或其他类型小说的框架。这个框架的好处是:一方面能把一部分被短视频、短剧拐跑的读者拉回来;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作者的个人表达。不只悬疑推理这个类型,还有科幻、奇幻,像陈春成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内核是严肃的,但其中也借助了不少科幻、奇幻等元素。
生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通俗文学合流了?
战玉冰:这要分两个维度来看。首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非对立,甚至是可以转化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本来就是给大众看的,《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里就有不少八卦剧情。英国作家狄更斯当年也是通俗作家,他的《雾都孤儿》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主要读者是伦敦的家庭主妇。包括金庸,从通俗文学代表到进入学术殿堂,最近几十年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经典化了。所以雅俗的界限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区分。
当然了,你是想借助通俗的外壳,表达一些严肃的东西,还是就想讲一个通俗的故事,让读者爽一下,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但在中间地带的创作者往往就不那么容易区分,比如很多类型文学作者也会在作品里探讨一些严肃议题。
生活周刊:作家写悬疑推理小说是要把读者拉回来,重新建立和大众的联系,不过在短视频、短剧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是否可能,小说这种形式会不会被取代?
战玉冰:这我无法预料,不过可以简单说说我的看法。一方面,读小说需要主动参与。首先你要读懂文字符号,然后进行解码,将它们转化成语义,最后在脑海里构建画面、串联情节。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思考过程,促使人走向内心。而短视频、短剧,也包括一些奇观电影,直接给观众以官能性刺激,不太需要你思考,让你在视觉表象的连续冲击中“目不暇接”。从这一点来看,文学对于打开人的内心深度世界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另一方面,不同媒介有不同特性,有些表达只有文学才能承载。比如《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林黛玉、薛宝钗以文字的形式来呈现可能是最好的,一旦具象化,变得可见了,也就意味着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哪怕是属于类型文学的本格推理小说,其中经常运用的叙述性诡计或建筑诡计,魅力正在于文字所营造的逻辑迷宫和静态推演,高度依赖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思维互动,恰恰不适合视觉化呈现。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侦探小说史、类型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等。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