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钓起世界之重——关于《钓鱼城》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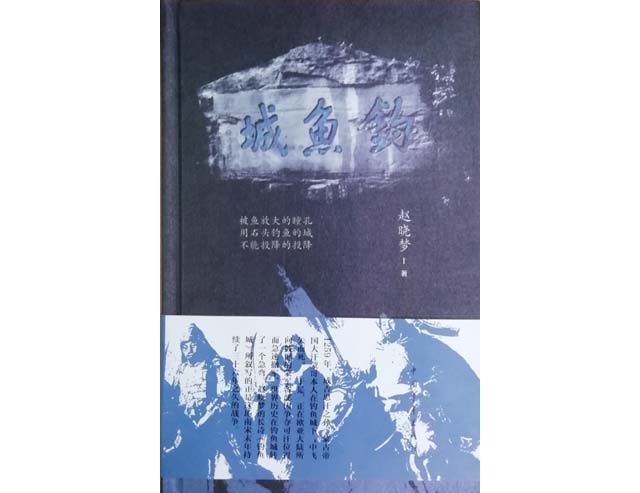
□李敬泽
钓钩虽小,但钓住了大鱼。“钓鱼城”也不大,但在历史上曾使天地为之惊、鬼神为之泣。赵晓梦做了个大梦,写了一部《钓鱼城》。
对中国的历史,我们还是知之甚少,现在网络史学又特别发达,对我们共同的过去经常会有一些破碎的、简单化的、知其一懒得知其二的刻板认识。比如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就打仗而言,宋朝很没出息,南宋尤其没出息,因为它毕竟是彻底输了,灭了国。其实客观地说,南宋是能打的,打得还是不错的。当年蒙古大军向南、向西,一路打过去,所向披靡,在前现代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平地上没有敌手,他们唯一的障碍是大海,打日本没有成功。这种情况下,南宋打得是不错的,很顽强。1259年,大军南征,重庆这个方向是蒙哥大汗亲征,湖北那边,忽必烈打襄阳。结果钓鱼城这边坚决顶住了,放在全世界来看都很不容易,一点不丢人。襄阳那边也是苦战好久坚决顶住了,不是靠郭靖郭大侠,当时南宋的将军不是白给的,南宋的士兵也不是白给的。
蒙古人的战争具有世界规模,那是前现代的世界大战,一边是南下灭宋,另一边已经到了伏尔加河,到了中东。所以,钓鱼城之战,久攻不克,蒙哥死在军中,确实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总体上迟滞了蒙古的攻势。
我记得以前乱翻书,有件事印象很深,说旭烈兀本来要打埃及,两军交战,互相都看得清楚了。这个时候忽然蒙古人撤了,拨马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旭烈兀接到了蒙哥升天的消息,要赶紧回来争夺汗位。
在这个意义上,钓鱼城之战是一个世界性事件,一根钓竿钓起了世界之重,改变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命运,比如无此一战,蒙古大军很可能就冲到埃及北非去了。
我们历史上是有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至今我们还不熟悉,还没有充分地进入我们的历史意识。现在有多少人能说出当时钓鱼城守将的名字?恐怕是很少。
所以,晓梦选的这样一个题材非常有价值。当然,这个题材对他来说,不是外在的,不是纯历史,他就是钓鱼城的人,这对他来说同时是个人记忆、个人经验。
写一部《钓鱼城》一定特别难,此事庞大而遥远,传统上只有以史诗那样的规模和尺度才能把握它,但也很难想象一个现代诗人写一部《伊利亚特》。现代诗人更倾向于举重若轻,一根钓竿钓起世界之重,而不是直接移山倒海。晓梦就想了一个很巧的办法,九个人、九个视角,三个人一组,攻城的、守城的和最后开城的。和传统史诗不一样,《钓鱼城》不是叙事性的,九个人都是内心独白,打开每个人的内在性。
于是,这样时间持续很长的、非常复杂的大规模事件,通过这九个点被透视出来,而且把整个事件心灵化了,变成了不同人物的内在体验。换了我,我也很可能用这样的办法,而晓梦把这九个点都写得相当充沛饱满。
但叙事性与抒情性怎么达致平衡,这始终是个麻烦。有的历史事件属于不言自明的公共知识,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你写一部三国的长诗,那么少叙事而纯任抒情,这是可行的。但钓鱼城这段历史大家不熟悉,直接读这个文本就会比较困难。晓梦削弱甚至剔除叙事性,这是对史诗传统的大胆背离。史诗书写大规模的人类行动,行动就是叙事,你就要讲故事就要交代来龙去脉,这一定是外在的、总体性的视角,游吟诗人或者上帝的视角。现在晓梦把视角放到了每个人的内部,是主观的、有限的、当下的,力图从内在性抵达史诗效果,这非常大胆,也很冒险,这就面临如何提供一个总体性叙事背景的困难。或许还可以再想想办法,比如这九个人是主歌,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个超越性的副歌,调子也不一定是主观的,甚至可以是白发渔樵的,是牛背牧童的,由此提供一个总体性、背景性、具有时间纵深的视角,把九个当下的视角串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九个人的内部空间能不能充分打开。对晓梦来说,真正的考验是,这九个空间能不能有内部的丰富性,这九个人相互之间能不能构成对比、冲突和对话。这很重要,保证整个《钓鱼城》形成一个壮阔的又是复杂参差的整体。晓梦对此颇具自觉。比如蒙哥的视角就是草原的视角、草原的感受;余玠则是农耕之子,是农耕文明中的士大夫,这里有世界观和感受力的强烈对比。《钓鱼城》有力地展现了九个不同视角、九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对照、参差、冲突、对话,这是它特别成功之处。
晓梦或许还可以打得更开,胆子还可以更大,让这九个人有更强的对话性,甚至展开争辩,这种争辩倒不是一问一答,而是世界观的无形争辩。比如蒙哥的世界观是空间主导的,一往无前的,地有多远马就要踏多远,风吹到哪儿我的马就要到哪儿,这是一个草原大汗的世界观。余玠的世界观是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这样的一个儒者,不动如山。发生在钓鱼城的就是不同世界观的冲撞对决,这样的对决,如果展现得更突出、更鲜明,可能更有力量,更有一种抒情的史诗性。
还有最后,王立要投降,还有熊耳夫人,都面临抉择。三个人参差对比,把那种艰难表现得特别有力。但是这种对比和对话也许还可以更尖锐更宽阔。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决断降或不降,不仅仅是权衡现实的各种可能性,而是内心幽深惨烈的天人交战。
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临安已经陷落了,已经另外立了少帝了,皇帝正在流离,正在逃亡,这个时候张珏做了一件事特别有意思,简直就是超现实的。他在钓鱼城给皇帝修了一座行宫,还派出人前往东南沿海寻迎少帝。我不知道张珏是怎么想的,他是真的觉得这事儿可行,流亡的皇帝会来,还是说我就是要立起这个宫,使皇帝的不在变成在,皇帝在这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皇位,而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认同。张珏这个人太不简单了,他的坚守和被俘都是宽阔深邃的,涉及人生和世界的基本意义。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历史中的这些人、这些英雄,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内心之浩瀚,真的是比我们现在的想象所能抵达的更为雄奇。
和王立相比,熊耳夫人是个女人,在战乱中颠簸、受难的女人,而且是我们河北女人,燕赵儿女,北方的、具有辽金背景,她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和想法肯定很不一样。这样一种内在性的多声部的交响,正是晓梦选择的这种形式的力量所在。
有朋友说,赵晓梦你写了《钓鱼城》,你别的诗都撕了吧。朋友有时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但是这里有一个意思我是赞同的,我也认为《钓鱼城》没有写完,《钓鱼城》不能画句号。像《钓鱼城》这样一部书,应该反复写、反复斟酌,不断丰富它、扩展它。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晓梦确实可以把以前的诗都放下,慢慢写《钓鱼城》。现在这本《钓鱼城》是第一版,以后可以写到二三四版,写到八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伟大的史诗,铭刻着我们民族的英雄业绩,同时又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时间、空间、历史、文明、生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刻省思。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