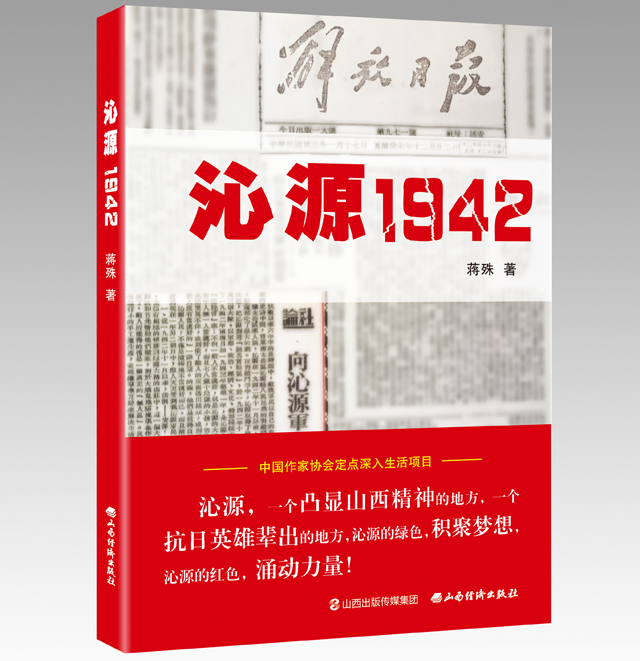品读|我就不去远方了——《他人史》序

□大解
一
1957年夏天,我出生于燕山东麓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里的茅草房占一半以上,只有少部分瓦房,冬天下了大雪以后,屋顶上积了厚厚的雪,整个村庄就像童话世界。村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居住在山村里,很少有人走到远方。在山村的外围,远近都是山,山的外面是群山。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村里的人们并未感觉到偏僻、落后、贫穷,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仿佛生活原本就是如此,就该如此,因此人们安心地在有限的区域里耕作和生死,世代绵延不绝。
越是封闭的地方,人们的想象力越丰富。在我的故乡,似乎人人都会讲故事,许多故事在流传中变成了传说,过于久远的传说就渐渐变成了神话。不是人们善于虚构,而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会越传越离谱,最后借助神话的翅膀飞起来,构成一种集体的幻觉,甚至成为精神存在。
远景一旦超越了现实,就会成为人的精神向往和归宿。因此,在一个小山村里,幻想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似乎只要有粮食和传说,人们就能活下去。
我就是在这样的山村里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直到二十几岁才走出去,进入了城里。可以说,我的人生入口非常小,小到方圆十里以内,在那小小的山村里,不存在整个世界,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写了四十多年诗,如果追查其精神来源,就会露出故乡的炊烟和土地。故乡是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源头。那里的一切都适合我开挖和抓取,也容易散开,弥漫在语言的世界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浪费甚至忽略了属于我的独特资源,把童年给予我的神话种子放在一边,而去试图寻找生活中的非理性。为此我写了四百多篇寓言。但我总感觉不过瘾。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隐藏在我的生命里,没有显露出来。直到2019年初,当我忽然写起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出口。
在小说中,我可以用语言复述我的故乡,深入到农耕记忆中,把深远的历史重建一遍,展现出那些被人忽略的、消逝的,甚至是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用文字创造出一种语言的现实,以此构成历史的多重性和丰富性。在语言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存在的,语言不仅是抽象的符号,也是高于生存的实体,它在超越现实时所释放的能量和展现出的精神景观,会让我们惊讶地发现,世界不仅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我喜欢作品中的虚构和飞翔感。
因此,在人们向往和寻找诗和远方的时候,我就不去远方了,我在近处转转。我愿意沉浸在我的故乡这个小地方里,甚至,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我甚至认为,语言才是文学的故乡,有着无限空间和可能性。
二
在我的故乡燕山地区,人们所说的生活,不仅仅是指发生在地表上的事情,也包括天上的事物和地下永居的先人们,人们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万物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因此,生活是漫长的,也是无边界的,一个人从生到死只是个短暂的过程,更多的时间是在死后,住在地下,放心地沉睡,或者转世为人,也许成为别的动物或植物,继续生活。
无穷无尽的生活,实际上是把时间看成了永恒,不再有尽头。在这无限膨胀的时间里,人的生命形态也是动态的,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每个人都不只有一生,每个人都有无数个生命。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一个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生命在运转和更替中实现了永生。
反映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小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表现方式和入口。可以说,我选择的入口很小,小到一个村庄,村庄里几个农耕时代的人物,一些简单到几乎没有故事的小段落,但是里面的气息和韵味却让我着迷。我不想也不愿意用心去描述世间的表象和矛盾,而是乐于试图通过普通人的点滴生活,深入到万物交互的复杂时空中,或者说穿透时间和空间,去探究那种混沌胶着的生死不明的状态。我的故乡,我的童年记忆,我记忆中的那些半人半神的人们,给了我丰富的创作资源。他们与天空和土地的关系,他们与乡亲邻里之间的关系,他们与死亡的关系,个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丝丝缕缕,纠缠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每一条线索都十分悠远,每个人都面目模糊,却无不散发着不可名状的神秘气息。
记忆再遥远,也有回溯之路;同样,肉体也并非完全封闭,总有一些密径可以通往人类的梦境。在万物联通的时空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事物之间以及事物本身的裂隙,恰好是文学的入口。由于我出生于燕山深处,一个古老的村庄向我敞开,它所保存的局部秘密似乎隐含着整个人类的幻觉。我努力用文字去接近这种幻觉,追溯那些渐渐散开的记忆,甚至不惜超越小说的边界,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寓言。
在我看来,小说和寓言的区别,主要是看有无诗歌和妄想混入其中,得其一便是分野。而我是个糊涂人,很难把这些宝贵的元素截然分开,因此文体变得不再重要。我可能要的是文学意义上的全部,包括那些无法归类的试错部分。正如我在小说中所写的人,不单单是他自己,他的身体和经历,也可能同属于他人,或者是整个族群。我在文学中记述人类的生活,不会绕开那些死去的人们,以及那些参与其中而又不能被我们看见的上苍的事物。正是那些缺失的部分在文字中得以显现,才使我们恍然大悟,生活原来也可以是这样的,而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
呈现生活中散失的东西,使莫须有的事物得以回归,还原生活的复杂原貌,应该是文学探索的价值和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一种乐趣。我乐于向神话索要配方,顺道去抢劫诗歌和寓言,然后不假思索来个一锅炖,熬出来什么就算什么。因此,我写这些短篇小说时从来不构思,在电脑上敲出第一行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行具体是什么,写着看。我写一篇短篇小说基本上在半天内完成,不会多于四个小时。在写作时,记忆中的许多东西都在涌现,好像不是我去主动选取,而是有一些东西不请自来,尤其是那些异想天开的地方让我开心,异想天开,天就真的开了。在我身上,不存在无形的枷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困住我的想象。我不喜欢边界,因此也就没有边界。
而这些,完全得益于我的故乡——燕山里一个贫穷荒僻的村庄。那里,生活着一代又一代朴实、勤劳、善良的人们。他们似乎是野生的,找不到源头,也看不出去向,活着就是生活本身,与天地自然构成一体。他们历经千年,构成流动的血脉,一些人倒下,总有一些人活下去,守护着古老的村庄,生生而不息。我只要想起这些人,想起他们曾经的故事,语言就会自动流淌,何须谋篇布局?这就人们所说的生活源泉吧。
然而,仅仅满足于现实给予的一切,是远远不够的,我要的是现实的成因以及现实外面的东西,那些虚无之处才是展开翅膀的空间,神也在那里游走和居住。我宁可放走千年的流水,也绝不会忽略飘过上苍的一片云彩,在精神上空,我知道那些致命的打击来自何处。闪电总是隐藏在那些看似普通的事物里,语言就是触摸和引爆它的开关。我对那些飞起来的事物,不只是神往,而是想去亲自试一试。我未必没有翅膀。
我的肆无忌惮的写作方式,显然是得益于我的生活经历。我在山村里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直到二十几岁才走到山的外面,如今燕山已经构成了我的生存背景,永远矗立在那里。故土不仅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精神的源头。而那些从未走出过燕山的逝者,已经定居在地下,我从来不把他们当作死者,只要我的心回到以往,他们就会立即复活,成为我笔下的人物。我认为,有这样绵延的山脉在我身后,有逐渐沉积的人们为我加厚原乡的土壤,我怎么去写都不算过分。我必须要写他们,我要写下他们的生死,甚至写出那些不存在的事物,为我们的生活作证。就是我在语言中真的飞了起来,我的故乡的人们也会相信,不是我的身体和精神变轻了,而是天空辽阔无边,没有一个展翅飞翔的人,岂不是浪费了空间,也误解了神的原意。
(《他人史》,大解著,2020年8月,作家出版社。大解,著有长诗《悲歌》,诗集《岁月》《个人史》《群峰无序》等,寓言集《傻子寓言》《傻子说》《别笑,我是认真的》等各类作品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
大解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