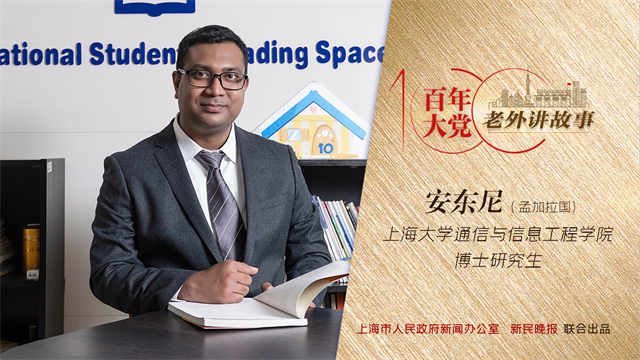让《赵氏孤儿》走进700年后的年轻人心里,这位“苛刻”的上海导演在想些什么?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
“赶快跑,赶快长。赶快长出你呐喊的喉结,强壮起你的肌肉,积蓄无敌的力量,挺起胸膛。生命对谁都一样,死亡也对谁都一样,都藏在你的路上”……
这是目前正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热演的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的返场曲。几日来,近两千人的剧场内座无虚席,观众为“大义”落泪,为良善欢歌。谢幕环节,当所有人高唱着“挺起胸膛”,欢呼声穿越千人的大剧场时,记者仿佛看到了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在这里上演时相似的热情。似乎,这样的热情也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未来升起一把火。
《赵氏孤儿》从创排伊始,就备受期待,不但聚集了郑棋元、徐均朔、方书剑、何亮辰等热度“出圈”的音乐剧演员,还特邀影视演员明道、薛佳凝 “跨界”。该剧从导演编排、演员刻画、音乐创作、舞美呈现,无不精致之极,首演当晚即冲上热搜娱乐榜榜首。
多年扎根原创,执着讲好中国故事的导演徐俊认为:“《赵氏孤儿》有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风骨、信仰与境界。在爱与复仇的母题下,我们仰望崇高,也要凝视深渊。”长达3年的精心酝酿,徐俊对演员,对剧本,对艺术追求近乎于苛刻。
日前,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对徐俊导演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他说,创作于700年前的《赵氏孤儿》,其对人性光辉的反思是中国传统文化通向未来的密码。“究竟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当命运让你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你是不是甘愿为‘家国’献出生命。《赵氏孤儿》中有非常崇高和大义凛然的部分,它可以激励我们当下的年轻人。”

历时3年,做了3万字导演阐述
《赵氏孤儿》首演大获好评,并不让人意外。徐俊导演耗时3年的心路历程,也都记在了他长达3万多字的导演阐述中。他为该剧设定的主题是《 “走向未来”的赵氏孤儿》,将这部元杂剧改编成音乐剧尚属国内首次,徐俊希望它从过去而来,走到今天,也将迎来未来。
在黑格尔极致悲剧美学和复仇的母题之下,徐俊也在反思一个命题:“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命运,并做出人性的选择。这当中,可以呈现很多层面的思考。它对人性的反思可以通向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当下。更何况,其中涵盖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能让当代青年读懂‘正义’。”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芬顿的话剧改编给了徐俊灵感。芬顿版最吸引徐俊的有两点:他遵循了黑格尔的悲剧美学,既有历史选择,也有自我选择。这个版本中的“程婴”与赵氏孤儿没有任何的关系,非亲非故,当为了保存赵族唯一的血脉时,程婴的善良,让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换取了赵氏孤儿的性命。这是一种正义的选择,他以“程婴”这个人物为基点,慢慢发展出后来的线索,让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物,不是空洞的崇高,而是有血有肉的。“程婴”这个人物的脉络线索是可信的,朴素真实的,这个剧本的内涵以及对人性的挖掘是深刻的。
第二点是,在任何一个版本的《赵氏孤儿》中,从来没有程婴亲生儿子这个角色出现。这个幼年惨死的孩子,其个体生命得到了聚焦。以往,他都只是一个符号。现在,让这个角色有血有肉地站在舞台上。于是,徐俊用“程子灵魂”这个孩子贯穿全剧,也是戏剧开场观众看到的那个游魂。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高子文认为,“古典作品的魅力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结论,而恰恰是因为它们提出了问题,让我们以一种现代的开放视野来面对过去。”这种观点也是徐俊在探讨“赵氏孤儿走向未来”的逻辑,过去没能解读“丰满”的人物动机,如何在当代让角色立得住,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可信性,才能潜移默化中,合情合理间为如今的年轻人注入思考的动线。

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未来藏在“匠心”里
作为导演,徐俊的严谨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在《赵氏孤儿》剧组排练的数月中,甚至是跨越整年的潜心钻研与琢磨中,不论该剧的主要演员还是群演,都在徐俊的精心调教之下,与角色深深嵌扣。
该剧核心演员11人,群演20人。在选角色的过程中,徐俊花费了大量时间。“我的观点是,谁合适就找谁演。音乐剧的门槛,就是首先要会唱,还要会演。比方说,选择郑棋元,我把他以往所有演过的作品都看了一遍。我再看他在声音方面的表现力,据此再来判断他饰演‘程婴’有几成把握。所有演员,这次和我接触下来,都发现我对演员的要求让他们‘疯掉’,舞台上一个手面的方向都不能错,转身的速度也要正确,这些肢体语言都有符号指向。以至于很多人跟我说,‘以前排戏蛮自由的,结果到徐俊导演这里,浑身上下什么都不对了。’ ”
在塑造人物中,徐俊要求演员要注意形体、眼神,随着剧情一步步发展,演员的整个表演状态都是需要变化的。剧中“程婴”有一个情节,跪在地上哭,他说出了16年埋藏在心底的真相。这时候的哭,徐俊要求郑棋元要做出“像气球被扎了一针之后,慢慢地瘪下去。” 据说,这一个动作就练习了很长时间。“我要发掘的就是一个演员的表演张力有多大,他能塑造角色的空间有多大。”徐俊补充道。
按照徐俊的创作逻辑,经典文本也需精细打磨。他经常要求演员撰写自己所饰人物的小传。只有对这个角色足够了解才能诠释好角色。“这是戏剧学院教学中、院团排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现在很多传统都没有了,这种好的传统,应该坚持下来。”
这次倒是例外,徐俊帮所有演员撰写了人物小传,打印出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让演员再此基础之上再来总结角色。排戏时的严谨,也让两个多月的排练高效缜密,每天都是按照通告进度来的,从没发生过改变,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出现“卡壳”。为此,徐俊很感谢上海戏剧学院7年的本科硕士生涯,他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轨迹也有着清晰认知。

为当代青年留下怎样的精神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徐俊有着一定的“艺术洁癖”。“到了我这个年纪,那些‘无厘头’ 的东西,我是坚决不碰的。”这些年,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徐俊创作并非高产,基本三四年才酝酿一部戏。他说,想明白了一部作品,就会投入往“深”里做。“我希望发出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也是需要被广大观众认可的。未来,我们的挑战依然很大,这是创作理念问题,是题材选择问题,还有就是你以什么样的精神为创作目的。”
《赵氏孤儿》在上海的首轮演出从5月27日持续到6月6日,之后将开启全国巡演。此次演出推出了大量的80元公益票,徐俊说,就是为了让更多当代年轻人走进剧场,理解家国情怀,有所思,有所悟。甚至开演前,主创团队还走进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就像经历过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男孩,长大后成为报效祖国的空降兵。这些年轻人在经历过生死大考之后,他的人格以及选择是不一样的。”
《赵氏孤儿》之后,徐俊给自己定了新目标:要做就做拥有“世界经典”的戏剧质量、高度、题材、人物的作品。他说:“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未来出路,就是要在保持戏剧艺术审美的基础上,给到当代年轻人什么样的精神内容,引发怎样的思考,这才是戏剧的魅力所在。”

【对话】
艺术的真谛应该是去创造
记者:《赵氏孤儿》进行音乐剧的改编还是第一次,如果遇到不同的风评,会有压力吗?
徐俊:这句话说起来,可能不太谦虚。在艺术审美上,我是不会向观众妥协的,我一定会追求我的理想。就好像说,你过分看重票房,过分迎合观众,你可能就会丧失在艺术上的追求。当然,这个过程,也有可能“粉身碎骨”。
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戏剧人,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戏剧究竟用来干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我觉得,戏剧的功能是对人产生一定的启发,当戏剧来启发你的时候,如果一味迎合观众,启发的意义又在哪里?戏剧的力量又在哪里?它应该站在一个超前或未来的视角,去对当下做启发。
记者:你所理解的“走向未来”的赵氏孤儿,应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徐俊:对过去的历史,对作品的年代背景要了解得非常透彻。我记得当时为了求证春秋时期的器物、服饰甚至行礼方式,我们都做了深入考证。只有当我们对历史有足够清晰全面的认识,你才知道当下我们要做什么。把历史传递到当下,这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一次连接。你做好了今天,也自然会知道未来我们要去做什么。过去、现在与未来,有一个相互间的关联,这是文化传承,又能凸显人性光辉,只要人不变,它也将通向未来。
记者:作为上海本土的戏剧导演,在创作取材和题材方面,有没有明显的地域属性?
徐俊:其实很难界定,上海这座城市本来就非常包容和开放,海纳百川是最能代表上海的标签。我觉得,戏剧也更应该有一种多元、包容的开放性。标签太过鲜明的话,是具有一定特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局限性。如果剧本本身是上海题材,那一定会把它做到极致,例如《永远的尹雪艳》用的都是会说上海话的演员,虽然他们都会上海话,但是演员台词训练依然耗时很久,我要求他们都要讲老式的上海话。
记者:你并不高产,但在创作方面,揪住你感兴趣的题材,便会一探到底?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
徐俊:音乐剧其实是一个有着成熟商业运作机制的戏剧类型,在西方也有成熟体系。可能就是出发点不同吧,我不是标榜自己,我真不是“冲着钱”去的,音乐剧的发展确实可以成为产业,一部剧能够成功,产生良好的市场效益,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在平衡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我首先还是会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我自己有一个信念,当你的出发点是做好一部作品的时候,往往财富也会向你靠拢。如果你只是想快速地获取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艺术的追求,赚钱也许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
记者:关于中国原创音乐剧这个话题,你觉得“原创”对于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来说,是条怎样的路径?
徐俊:现在上海的音乐剧市场非常热闹,其现象是多元的,音乐剧作为舶来品,国外引进剧比较多,作为超级IP,其中文译版也在国内很受欢迎,我们也有很多原创音乐剧;但是从目前整体质量来看,音乐剧作为一种歌舞类剧目,文本内涵会显得比较“平”,比较“浅”。反过来说,这条路未来应该去往何处,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原创音乐剧力量,对于戏剧人而言,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引进剧和中文版毕竟是西方的,也有着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但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艺术的真谛,不是去模仿,而应该是去创造。30年走下来,中国的音乐剧人也在慢慢探索建立中国的原创音乐剧体系。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原创,它应该成为中国音乐剧人广泛的认知,让创作者建立共识。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