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给对岸的父亲们——向迅《与父亲书》读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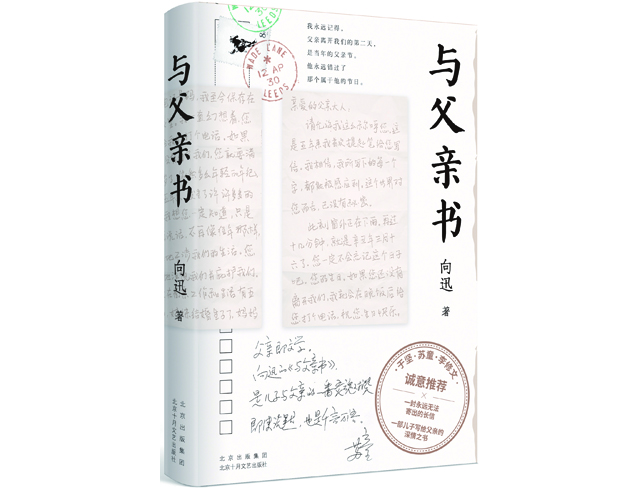
□耿凤
一
收到向迅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与父亲书》,是七月一个礼拜三的清晨。那天,我穿着一条因膝盖伤口未痊愈而不得不选择的不过膝的淡绿色裙子。在单位收发室堆积如丘的杂乱信件和快递缝隙中找到快递后,我边走边拆,这有些迫不及待的意味。很轻巧的一本书,与我们当初讨论过的封面别无二致,也如我的淡绿色裙子一样轻盈。不得不承认,在书这件事上,我总是挑拣,挑拣出版社,挑拣译者,挑拣谁设计的封面更得我心。这使我莫名欢喜。
在这之前,我已做好了泪眼模糊的准备,却没预料到向迅随手写的一句话就把我的防线击得如同碎屑,散落一地——“我们经历的一切,不仅仅只是成为记忆”。我用了三秒读完这句话,却几乎是瞬间用颤抖的双手“啪”地合上了书。我的淡绿色裙子不再轻盈。我的心跳加快。我甚至听见了它因触碰到隐匿已久、逝去已久的缥缈之事而发出的惊叫。我本就上楼还有些吃力的左腿被那声声惊叫趔趄了一下。我差点扑空。我的面前已没有一个父亲等着护我周全。
等我走进办公室坐定,给向迅发微信说看到那句话手抖了。他回复说——“抱歉。应该写句温和一点的”。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这句话给别人不一定合适。他说——“我们遭遇了部分相似的命运。故而有这么一句话,在给你时冒了出来。相信你能看懂”。我怎么能不懂呢!我必然是比其他读者更懂这句话的分量和意义。之前收到王单单的新书,其中有篇文章也是写父亲的。那天我坐在许多个架子鼓教室外的走廊里,整个走廊只有一把白色座椅,清洁阿姨看我捧一本书默默打开灯,前台的姑娘又摁响了中央空调的遥控器,发出的“嘀嘀”声瞬间被架子鼓的节奏感湮灭。我就是伴着架子鼓哽咽着看完这篇散文的。我就那么笃定地认为尽管地域不同,习俗不同,家境不同,语言也不尽相同,可我们终究因相同的遭遇成了相同的人——没有父亲的孩子。是的,是相同,不是相似。所以,我以为在向迅的文章里看到的也会是同一种“相同”,而事实是,不尽相同。
二
向迅不止一次对我说,写下来。最开始听着是随口一说,后来像是建议,再后来又像是劝说,渐渐地就越发增加了呛人的味道,飘在眼前想拒绝又被一丝欲望吊着,很强烈。我没有向迅勇敢,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不敢写。我害怕。仔细想来,我们认识的这几年,除了聊到父亲的话题时会不约而同地一本正经,容不得半点戏谑之词,其他时候都轻松地开玩笑。
在自序《锦书谁寄来》和后记《家书寄远人》中,我想我找到了他多次劝说我写下来的原因,这也是他这几年一直书写父亲的缘由:
——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记忆会越来越迷糊。我要通过书写的方式,让父亲活着,让他逐渐模糊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既是我理解父亲的方式,也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我不能忍受父亲与那些散落乡间的祖辈一样,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的记忆里,从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消失。
——在这封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的长信中,我试图与父亲进行一番马拉松式的长谈,像亲密无间的父子那样,像有过命之交而又惺惺相惜的兄弟那样。
哪里会想到,隔着一条大江和一条大河的两个人,竟在失去父亲这件事上有了交集。在向迅的笔下,那是怎样的一个父亲啊!每一篇里的父亲都是一个单独的父亲,每一篇里的父亲拼接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父亲。这个父亲年轻时脾性不好,这个父亲勇敢时像个英雄,这个父亲进城时局里局气,这个父亲生病时胆小拘谨,这个父亲不被他的父母所爱……父亲的无数个面矛盾地存在着,但在人类长河里仍能相依相偎,这才构成了他的一生。
三
看完《九月永存》最后一个字,我突然掩面哭泣,上半身不受控制地抖动。我用左手捂住了整个脸颊,仿佛怕被人看到我的无助,仿佛怕伸手抓不到一只渴盼已久的手。我的脸一定扭曲得面目全非——眉头紧锁,嘴角向下,一排藏在嘴巴里永远保持沉默的牙齿暴露无疑。我甚至努力克制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而正是这种克制才导致我的上半身抖动,不受控制地抖动,又近乎崩溃地抖动。事实上,房间里只有我一人。而十年前父亲的离开,也是一个九月。
等我渐渐安静下来,发现书脊的胶水已经被我刚才没有意识到的双肘支撑掩面哭泣和抖动压得裂开了,露出了间隔一厘米宽的订装线。我想跟向迅说一句抱歉,并告诉他我不是有意损坏了他送我的书。但终究没有说。是觉得任何语言都太过于轻飘。
事实上,不止这一篇让我有如此失态之举,而是近乎每一篇都让我的泪腺分泌出源源不断的泪水,有热烈的,也有冰冷的。尤其看到后记时,本来躺在床上举着书的我忘了膝盖的伤翻身趴了起来,那尖利的疼痛感毫无征兆地迫使我“嘶”出了声。我在看最后一篇文字时又一次哭了。哭出了声。比之前的每一次都痛快,像是释放,像是身体里无数条鱼儿冲破一道无形又厚重的门奔向广阔的大海。
我总能在文章里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段落找到仿佛被雷击中的点,然后在旁边写上几个字表达我那一刻内心的波澜。如此一来,神奇的一幕便会出现:一些记忆碎片在空中轻盈地飞起来,再慢慢聚集到一起——这些碎片拼接成一帧帧画面,每一帧里都有我飞起来的父亲,有那个不出汗的夏天和天高云淡的秋天。我说不好这些片段带给我的是幸福还是痛心。但我为这些因向迅的文字找回的记忆片段而真诚感激。我曾与向迅开玩笑:我如此认真地对待一本书,他是沾了父亲们的光。不知道他能否体味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该说谢谢的是我。
我决定写下来了。
四
在还剩《时间城堡》《无名之辈》这两篇文章未看的一个周末,我把《与父亲书》装进背包,带回了无极老家。其实《无名之辈》中的一章“H先生”先前已经看过,一次是向迅刚写完发我,看到一半去忙其他的事,后来也没继续看下去;再一次是这篇文章发在一家刊物之后。算上这次,是第三遍了。
母亲识字不多,却认出了“与父亲书”四个字,也可能只认出了“父亲”,这都说不好。她忽地抬头问我:“这是你写的吗?”我没敢看她,我害怕从她本就瘦削的脸上再看到任何一丝不安的神情。“不是。”我回答得利落而干脆。
“是别人写的啊。”她失望了吗?我不知晓。因为我没有看她的脸。
“向迅。一个朋友。”
我以为话题会就此打住,母亲却又从因牙质不好早早换上一口假牙而看上去有点瘪下去的嘴巴里抛出一个问题:“这是他写给他爸的吗?”
我说:“嗯。”也许我并没有把这个想说却紧张心虚到难以言说的字发出声音,只是鼻音在作祟。总之,她没有再说什么。她只是把端详了许久的这本书放回了原位。大概我看到了她内心有隐隐作痛的跳动,她也同样看到了我内心十分隐忍的难过。我们,只是心照不宣。
午饭后,我问母亲:“你和我爸有结婚证吗?”
她说:“有啊。不是本,是像奖状一样的。”
我问:“你俩一起去领的证吗?”
她把头一偏,又把有些驼背前倾的身子挺了挺:“不。你爸一个人去的。你爸有熟人,不用我去。像别人没熟人的,就得俩人都去。”
这才是我的父亲。他总是很有人缘,有很多朋友。我又问:“证在哪儿呢?”
她说:“早撕了。扔了。”
这使我诧异到瞠目结舌:“扔了?是在我爸走了之后吗?”
她脸上竟挂着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不是。那会儿你爸还在。”
“那为什么扔了?”我穷追不舍,我是想看看他们的结婚证的。我想看看1981年的结婚证上是不是也像向迅父母的结婚证一样没有粘贴结婚登记照。1981年,是我根据我姐的出生年份推算的,母亲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
“又没想着离婚。”她回答得云淡风轻。
五
我得坦言,这些天看向迅的书有些压抑,每看一篇就要缓两天。所以断断续续地,这本书从拿到手到看完最后一个字,花了整整二十天。我知道,这太长了。我甚至没意识到因为《与父亲书》给我的种种情绪已经影响到了他人。
我前面说过,我没有向迅勇敢。
向迅的勇敢,不只在于他敢写消失的父亲,更在于他走出了传统写作伦理的禁区——展现一个伟岸的完美的父亲形象。向迅把自己一颗想靠近并试图翻越和拆除沉默之墙又因父亲生病住院有些嫌弃不愿陪床的心剖开给大家看,他把一个“性格暴躁,拥有一段可能存在情感野史”和“不被父母所爱,像一个孤儿”的父亲暴露在阳光之下给大家看。这份勇敢很多人都不及。
我不敢说向迅的父亲是中国众多父亲的一个缩影,因为这个父亲性格暴躁,甚至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导致了“在他活着的时候,错过了一次次向彼此吐露肺腑之言的机会”。这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是无法想象的,这个父亲形象实在是跟在我身上把“满眼皆是你”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我的父亲大相径庭,但又总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一些雷同的父亲的影子。比如父亲生病后言语举止中的小心翼翼;比如“父亲最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嘱”;又比如父亲“被疾病日夜折磨,身体里塞满恐惧和无穷无尽的孤独”……
我们都是父亲以血脉的另一种方式遗留在人世的延续。向迅通过写作这条“可以通往对方内心世界的小径”,与自己的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相信长谈并未结束,父子之间的“终于哑口无言”会随着河流的流向慢慢梳理开。你对着河流说话,对岸的父亲对着河流说话——河流也会同你和父亲讲话。
这个夜晚,伴着我写这些字的是朱晓玫版的《哥德堡变奏曲》,此刻已是凌晨四点,窗外的雨下个不停,又播放到第25个变奏。
第25个变奏是黑珍珠,是这个曲子的核。
(散文集《与父亲书》,向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向迅:1984年生于中国鄂西,现居江南。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散文集《与父亲书》《谁还能衣锦还乡》《斯卡布罗集市》《寄居者笔记》等。曾获林语堂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等多种奖项。耿凤:供职于河北省文联,《当代人》编辑部主任,有诗歌、散文及访谈作品散见于报刊。)
耿凤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