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涤荡阴霾的剑,一盏照亮前路的灯——直击希望24热线的24小时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 施培琦/图、视频(文中除李群英和专家外皆化名)
“如果coco当时打了‘希望24热线’……”7月5日22点19分,距离知名歌星李玟因为抑郁症去世“官宣”一个多小时后,希望24热线志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希望24热线)的志愿者杨智发了一条朋友圈。
但世界上没有如果,杨智的“如果”也仅仅限于理论上的可能。因为他知道,即便coco拨打了这条热线,也可能由于多种因素无法接通。
同样在几年前,一名女大学生在轻生之际,曾尝试拨打希望24热线——400-161-9995,但是电话没有接通。“警方反馈了情况后,我们团队挺难受的,如果……”希望24热线上海中心执行长李群英的心里,藏着许多类似的不甘和无奈。
2012年12月,希望24热线这个民间公益机构在上海开线,从2014年起,全国24个城市都陆续开通了接线室,这条热线转型成为全国热线。时隔11年,这条24小时危机干预热线仍在艰难运转,但经费匮乏、环境恶劣、志愿者接线员人数锐减等种种问题让上海中心的维系步履蹒跚。
“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还会不会有‘如果’?”李群英对这条热线的未来,充满着迷茫与担忧。

◤ 大夜班 ◢
“我做志愿者的这几年,高危电话不是特别多,但是每一次发生都是惊心动魄的,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些绩效,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情绪垃圾桶’,但是总有人要来做这些事情,总要有人接受这些情绪,对吧?”
1987年出生的杨智住在浦东三林地区。7月8日傍晚,在家中吃过饭嘱咐妻子和11岁的儿子早点休息后,他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急匆匆地赶往自己上“大夜班”的工作地点。
希望24热线位于灵岩南路上一个老旧的园区内,距离杨智的家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
“要相信每一个来电者说的都是真的;千万不要拿起电话就说‘你好’,因为很多来电者并不好;如果能够被我逗笑,那肯定算不上高危……”
一路上,杨智会默念几遍接听规范以及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并提醒自己“一定要控制情绪”。
周末的园区冷冷清清,门卫对小摩托挥了挥手。18:00,杨智的摩托车准时停在了一幢5层楼的商务楼前。
商务楼底层的布局略显局促,正对大门的狭小楼道只能允许两个人侧身通过,昏暗的灯光照射在楼梯上,颇有港片的味道。
走上二楼,同样是一条阳光无法直射的狭长通道,两边的门上零零散散地挂着许多小公司的铭牌,希望24热线在这里算得上是“大户”——因为他们占据着两个门洞。
然而,对于志愿者们来说,门洞里面是完全和“大户”不搭界的场景: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了两个接线工位和几个文件柜,工位的边上则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为了能够让上夜班的志愿者有地方休息,房间的角落里还搭了一张沙发床。
“环境的确不好,我们也习惯了,之前搬了好几次地方。”
此时,急着上楼的杨智刚刚结束一场30分钟的电话“博弈”,他摘下破旧不堪的耳麦,指了指放在地上的纯净水桶问记者:“喝水吗?”
还来不及等到记者的回答,接线室内的电话又骤然响起:“喂,希望热线。”杨智继续戴上极度不适的耳麦,立刻回到了工位前。
电话的那头却没有传来一丝声响……
这样的电话,杨智接到过无数次,来电者其实戒备心很强,会根据接线员的性别、语速、语气等判断要不要继续说话,“当然也有电话接通后一声不吭一个劲儿哭的……”
这几年,来电者中95后、00后、10后的比例明显增多,这一切缘于某个大V的视频——她说自己曾有一段最难熬的日子,是希望24热线帮她走了出来,这是一条有温度的热线。
大V的无心插柳让这条有温度的热线咨询量暴涨,但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电话拨打量上去了,但骚扰电话也同时激增,希望24热线运维费比往年翻了几倍,“400电话升级、补bug、后台服务器的管理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些都是我们自掏腰包。”正准备“下班”的上海中心执行长李群英有些无奈。
运维和经费并不是杨智关心的问题,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KPI”——一晚上能接到多少个有效电话。
凌晨一点半,一名吃了四粒急性安眠药同时患有抑郁症的女孩第二次打来求助电话,杨智警惕性地抬头,看了看贴在电脑屏幕下热线所在辖区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号码。
一旦判定高危,他会立即报警。
经过20分钟的沟通和评估,这个女孩并不算高危,但杨智还是认真记录了她的相关信息,并在电脑系统里进行了备注,为的是方便后续的志愿者能迅速判断可能出现的第三通电话的危急程度。
“我做志愿者的这几年,高危电话不是特别多,但是每一次发生都是惊心动魄的,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些绩效,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情绪垃圾桶’,但是总有人要来做这些事情,总要有人接受这些情绪,对吧?”
对于希望24热线的志愿者来说,那些倾诉、抱怨、发泄的电话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求助电话,在危险等级里评分也不高。只有在电话的那头不断对自我进行否定、对未来产生迷茫、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才是志愿者们最想要帮助的对象,而在电话的这头——他们就像一柄涤荡阴霾的剑,也像是一盏照亮前路的灯。
◤ “青春美少女” ◢
“这是最后一个电话了,按照流程要到早上8点,但我接不动了。”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这样的传播是常态化的,而不是零散的。”
渴望更多的在校大学生也能参与进来,加入到小丸子剧团,而不仅仅是一群70后80后“老阿姨”,涂着厚厚的脂粉在舞台上扮作“青春美少女”。
“原来真的有24小时热线,这个点打扰您休息了吗?”清晨5点,希望24热线的电话依然没有断过。
“这是最后一个电话了,按照流程要到早上8点,但我接不动了。”连着工作11个小时后,杨智关闭了接线通道,拿起自己的摩托车头盔,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同时也是希望24热线上海中心为数不多的男性志愿者,杨智和另外两三名老师,扛起了夜班的重任,但也仅限于一个月的寥寥数次。
早上8点,两名接班的志愿者来到了接线室开始工作,这也意味着,从杨智的离去到新的志愿者上岗,有三个小时的空当,而一周夜班的空当,因为人员短缺的问题,更是高达四五天。
缺人,永远是这里的常态,晚上缺人,更是痛点中的难点。虽然这条全国性的救助热线还有其他省份的中心帮着将夜间的电话进行分流接听,但仍旧掩盖不住上海中心缺兵少将的窘境,而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无助的夜晚恰恰是情绪宣泄的高峰时段。
杨智的“接班人”是两名40多岁的志愿者,曾在银行工作的刘锦艺是资历最深的排班团长,几年前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她辞了职,也卸任了排班团长,但始终没有离开接线员的岗位。
上午8点40分,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打来求助电话。
“我太痛苦了!”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我不想活了。”
经过长达半小时的疏导和沟通,刘锦艺和男青年隔着电话,彼此伸出小指和大拇指“拉钩”,签署了一个“隔空生命协议”。
一个小时后,和她搭班的志愿者陆小宝也接到了一个高危个案。对方是一名患有严重抑郁症、陷入生活困境的青年。电话那头,男人喃喃低语:“coco李玟也是因为抑郁症走了……”
陆小宝按照流程循循善诱,结束之际,男人语气变得不再沉重,最后缓缓吐出三个字——“谢谢你”。
这三个字给不了陆小宝任何物质方面的收获,却是撑起她放弃休息时间来这里接线的动力,你甚至看不出,电话里铿锵有力、侃侃而谈的她,刚刚接受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
自从2021年加入志愿者团队,服务两年多后,40多岁的陆小宝多了另一重身份——热线宣讲团团长。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头衔,有的时候甚至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招募宣讲团的志愿者时,陆小宝会大段大段地码字,像打了鸡血一样呼吁大家加入,但这些话像石头扔在大海里一样,溅不起一朵水花。
除了接线团、宣讲团,希望24热线志愿服务中心还有一个面向青少年儿童做心理普及的小丸子剧团。前不久,因为人手不够,陆小宝扎着丸子头,客串了一回剧团的角色,通过舞台剧的方式为一年级小朋友讲述如何控制情绪。
没有鲜花亦没有太多的掌声。有人说她傻。但私底下她有自己的坚持,原来,从小她就看到周围一些不完整家庭的同龄人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我没那么伟大,只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微光,帮到尽可能多的人。”
只是,她打心底希望,上海中心这条倾注了数十名志愿者心血的热线能有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这样的传播是常态化的,而不是零散的。”
她也渴望更多的在校大学生也能参与进来,加入到小丸子剧团,而不仅仅是她们一群70后80后“老阿姨”,涂着厚厚的脂粉在舞台上“装嫩”,扮成“青春美少女”。

◤ 填不满的排班表 ◢
“走出接线室,就要脱离志愿者的角色,回归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坚持不做线下引流,一方面是保护来电者的隐私,另一方面更是坚守自己的初心。”
“因为来电者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和‘社会’这个整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说陆小宝是“新人”的话,肖元芳则是陪伴希望24热线11年的“元老级老法师”。
2012年,肖元芳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第一期培训班,当时礼堂内座无虚席的场景历历在目,她领到的是“61号”学员证。11年过去了,昔日的小伙伴剩下不到10人。
下午1点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接线室,换班后的她埋头接线,认真做个案记录。当天下午,她接到四五名抑郁症患者打来的求助电话。
这样高强度的接线工作她已经司空见惯。她曾干预过一名在地下室想要轻生的求助者,愣是花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力劝对方放下自杀念头,回到家能量被耗尽的她瘫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事后,她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求助者,甚至出现了过度介入的情况,“要不要跟进?”也在志愿者中引起了一阵波澜。
和杨智口中“相信来电者说的都是真的”一样,放下,同样是这群志愿者所要学会的基本素养,“走出接线室,就要脱离志愿者的角色,回归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坚持不做线下引流,一方面是保护来电者的隐私,另一方面更是坚守自己的初心。”
热线为何留不住志愿者?肖元芳认为,问题是多重的。没有任何补贴的志愿者能坚持下去非常考验人性,“我们希望社会、政府能给予公益性的支持。”她也曾向执行长建议过,能否效仿其他热线,让志愿者能不受空间和设备的限制,在家接听电话,但因为匮乏经费以及技术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和肖元芳搭班的接线员,已经退休的马素素的初心很简单——不荒废所学,助人亦助己。2015年拿到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她希望给更多的人带去力量。
马素素心中也有类似肖元芳同样的纠结,有的来电者属于循环个案,几年中多次拨打。她建议:“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多次来电者主动做一些随访?”
然而,转身看了看局促的接线空间以及永远填不满的排班表,马素素有些悻悻然。
下午5点,花了整整45分钟的时间,另一名接线志愿者小丹终于挂了电话。她长吁一口气:“好难。”
来电的是一名“啃老族”,她试图帮他重回生活的正轨。
今年年初加入热线的小丹,每次值班都需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的地铁。谈及为何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时,小丹说:“因为来电者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和‘社会’这个整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尽管这里的每个志愿者都为自己的社会价值感到骄傲,但社会中的价值互换以及共赢,在这里几乎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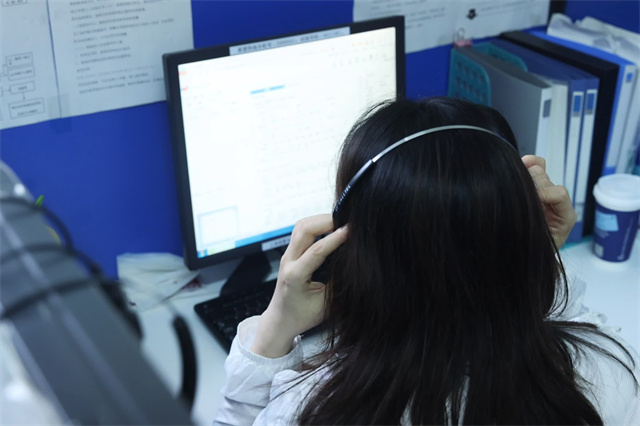
◤ 变与不变 ◢
“这条热线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志愿者是利他性行为,一旦给予补贴,就属于交换性行为。正是因为这样纯粹的要求,才使得这条热线能坚守初心。”
“公司谈的是利益,这里谈的是情感。很多人无数次想过离开,留下来的志愿者责任心大于爱心。”
“尤其是这几年,我有一种无力感,感到个人无法再为热线创造更多的价值。希望找到年轻的接班人或者机构接手热线,让它踏上新征途。”
起初,不少志愿者也有埋怨自己“待遇过差”,私下,更有不少人吐槽——要成为志愿者还需要接受培训,需要支付数百元的培训费,获得统一颁发的资格证书才能上岗,不解和质疑多多少少在小范围流传。
该热线上海中心执行长李群英对外有着统一的解释:“这条热线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志愿者是利他性行为,一旦给予补贴,就属于交换性行为。”
然而,每一次静下心来自省,志愿者们的困惑,同样伴随着李群英。
最近,李群英又拿到了催缴房租、物业管理费的通知。办公环境简陋、没有志愿者经费、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等种种问题,让这名为热线付出11年时间的51岁中年女子看上去有点憔悴。
“尤其是这几年,我有一种无力感。感到个人无法再为热线创造更多的价值。”她告诉记者,希望找到年轻的接班人或者机构接手热线,让它踏上新征途。
曾参加过希望24热线筹备阶段的一期培训,目前是上海市心理热线志愿者、资深咨询师的郑老师,对于李群英的窘境深有感触。郑老师回忆说,最早的几期是公益培训,但永远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势必会面临志愿者不断流失的窘境。
郑老师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建议,“如果希望走纯公益路线,看能不能和最想进行危机干预的政府机构合作,比如现在12开头的一些热线是分很多种类的,有青少年、法律、消费者维权等,有没有可能争取一根危机干预的热线?如果无法走纯公益路线的话,就得找机构资助或者自行融资,用心理学养心理学,用商业养公益。用爱发电,只能一时,不可一世。”
心理咨询专家、上海体育大学教授贺岭峰与郑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贺岭峰认为,公益不是完全免费的代名词,民间组织做公益也要遵循一套运行模式。以希望24热线为例,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原因是缺乏经费的支持,如果走公益路线的话建议找一家基金会合作给予基本的保障;如果走商业运营路线,则要设计一套商业模式。
“我感觉现在他们将商业和公益混合在一起。个人觉得为了运维热线,收取志愿者的培训费是不合适的,这一模式不太可持续。志愿者不能又出钱又出力。”贺岭峰建议,“将公益和商业清晰地划分开来。比如心理学的培训可以做成免费模式,热线也是免费提供咨询的。但可以将线上的资源引流到线下,为开展商业活动、为企业做EAP服务等提供品牌背书,也可以直接寻找基金会做支持。”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童潇肯定了希望24热线的意义,他说:“社会上大家压力比较大,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热线为有抑郁情绪的人们提供帮助,避免了一些悲剧发生,是一件好事。”
童潇表示,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方案,比如很多高校有心理学系、社会工作系,可以和他们合作,为热线输送志愿者,“首先建议通过广而告之的方式扩大热线的品牌影响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可以通过寻求社会和政府的帮助,比如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场地租赁等问题。有了经费,可以让志愿者少一些后顾之忧,专注于用自身的本领为来电者提供专业性的咨询。”
截至2022年12月,热线开通十年,共有来电70多万通,其中有效电话42万余通。但近几年由于接线员人手不足,接通率常常不满50%。
“公司谈的是利益,这里谈的是情感。很多人无数次想过离开,留下来的志愿者责任心大于爱心。”对于志愿者的期望,李群英看着简陋的接线室,不知如何作答。
“变”与“不变”两者之间,有时很难真正分清楚究竟哪一个更难。因为分不清难易,也有无从突破的局促,更因纠结于商业引流和个人隐私之间那道天然的沟堑,于是李群英和整个团队习惯性地选择“不变”,依然坚持至今。
7月9日下午6时,当肖元芳和马素素走出接线室后,晚班和大晚班的志愿者一栏依旧是空白的,少数能“顶上来”的志愿者中的杨智正陪着11岁儿子在家里看球。
接线室的大门,14个小时之后才能开启,热线上海中心那条可能创造无数“如果”的电话,也需要14个小时后,才会有人接听。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 施培琦/图、视频(文中除李群英外皆化名)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