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艺术评论犹如绘制航海图,好的评论像一座闪光的灯塔,为观众指引着方向

沈语冰在第九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现场发言。本文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沈语冰有一次在上艺术评论课时,提到自己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拿到了一份艺术批评参考书籍清单。他说,这就像一张航海图。这个有趣的比喻让在现场听课的学生庞铮豁然开朗,“这门课对于我来说,也像是灯塔一般的存在。”数年后,她获得了第八届国际艺术评论奖二等奖。艺术评论作为介于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重要存在,是将观众引入歧途,还是成为一座通往理解艺术品的桥梁,甚至是一座美育的灯塔?这取决于艺术评论如何写。
“清晰”是评判艺术评论好坏的标准
在决定写艺术评论前,首先要厘清一个问题,即艺术评论究竟是写给谁看的?看似明知故问,实则不然,不同评论家对不同受众的预设造就了理解偏差。比如有的评论人忌惮艺术家本人看到过于清晰的评论,使其产生被一眼望穿的失落感,因此行文中总是刻意留有余地,故弄玄虚,加上一大堆艺术理论甚至哲学术语,最终形成极其晦涩的文本,难免让普通观众如坠雾中不辨方向,无形中把观众推向了与艺术越来越远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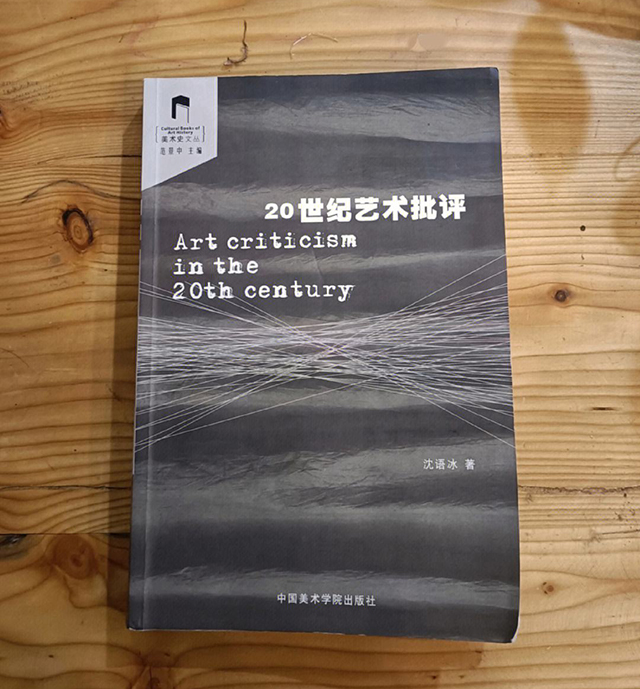
沈语冰作品。
对此,沈语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艺术评论一定是写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看的。”这意味着艺术评论必须是独立的,这是艺术评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写评论时完全不需要征得相关艺术家的同意。此外,还要尽可能清晰地将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或是某位策展人的展览,进行实实在在的独立评论,绝非巧言令色把对方吹捧一通。在沈语冰看来,“清晰”绝对是评判一篇艺术评论好坏的标准。因为只有清晰的表达,才能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对作品的理解深度,“深度可以分很多层面,比如说除了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外,能否结合一定的理论,将作品说得更加透彻。”当然,结合理论显然需要具备深入浅出的功底,“如果只是一个理论接着一个理论,将批评变成理论的操练,那肯定是不行的。”
正如庞铮在今年第九届国际艺术评论奖征集过程中,作为往届获奖者受访时谈到的常见疑问,“艺术最重要的是个人感受,自己看就好了,听导赏会不会过度解读,反而消解了艺术的神秘和亲密性?”她所热衷从事的艺术展览导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和艺术评论相似。她表示自己非常认同沈语冰在其新书《图像与爱欲:马奈的艺术》中所说,人们看画往往不局限于“我喜欢”这样纯粹的感官层面,多数情况下,他们还会做出“这件作品很好,或者很差”的审美判断。“拥有并使用增加绘画认知的‘工具’就很有必要了,专业的艺术导赏可以让听众学会绘画鉴赏的基本方法,使得听众可以更好地像沈老师说的那样‘趋近绘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从绘画延伸至更加广泛的艺术形式。
由此可见,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借助艺术评论之类的“工具”来提升个人艺术鉴赏能力。沈语冰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美学、现代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中西比较艺术与比较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他的排序中,艺术评论、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哲学是一个依次不断抽象化的美育上升通道,“美育需要扩大知识面,不能光讲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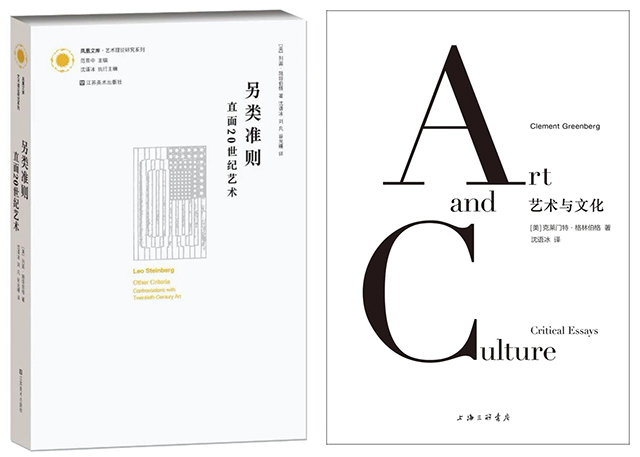
沈语冰翻译作品。
艺术评论需要有独立批评的声音
显然,艺术评论既是批评家个人的艺术鉴赏,也是对其所感进行反思、分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观众读到良莠不齐的艺术评论也就在所难免。这是当下艺术评论中存在的问题之一。不过,在沈语冰看来,当下艺术评论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艺术评论并没有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因此在艺术界的博弈中,它暂时处于一个失语状态。”沈语冰表示,在艺术场域中,政治、资本、智力三方博弈后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创造性系统,独立的艺评和艺术史研究等智力的缺失,会打破艺术生态的平衡。当记者追问能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失衡状态时,沈语冰说,他不想说得过于具体,以至得罪艺术家或艺评家,不过当下非常热闹的一个事件,即艺术家抄袭事件,或许与独立艺术批评的缺失有关。
而就批评文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批评不是堆积形容词来炫耀自己的写作能力,更不是以过多的修辞来抒情。批评从本质上来讲要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沈语冰表示,这座“桥梁”首先至少要安全,不能为了搭得漂亮而不顾安全,否则公众就有可能被带进坑里了。但如今看到很多艺术评论都存在着过多形容词、专有名词,以及长句子,且句式单调,还有长篇累牍的“掉书袋”,又辞不达意的情况。他表示,“这是对艺术评论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这种现象不仅在艺术评论中常见,在普通写作中也屡见不鲜,他坦言在学生论文中也常常遇到此类问题,因此,艺术评论最终还是要指向写作能力。
沈语冰为记者讲述的这些原则,也是他用来考察艺术评论的重要指标。当谈及自己的两名学生曾经在国际艺术评论奖取得优异成绩,他直呼不容易,每一届海内外几百篇艺术评论中最终选出一名一等奖和三名二等奖,而庞铮正是二等奖得主。他的另一名学生也曾入围中文前10,表现也相当不俗。截至记者发稿,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久事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征集环节已接近尾声,问及是否有学生参与,沈语冰笑称,“他们都不肯告诉我。”但他同时也表示,“获奖也许是一个类似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但重在参与,不妨把投稿视为一次锻炼的机会。”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