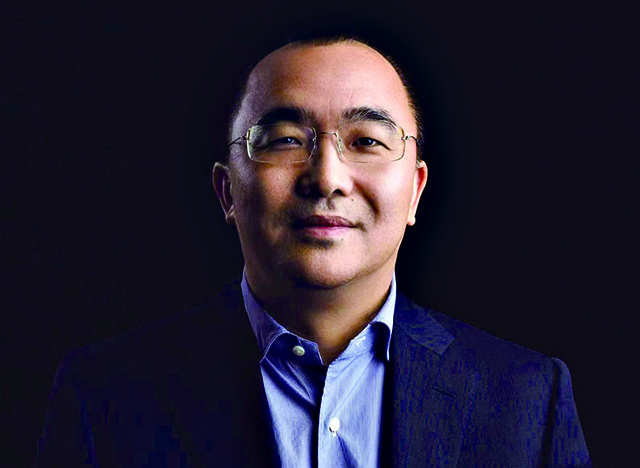荐读|带露的朝花——吴梅英《小村庄》读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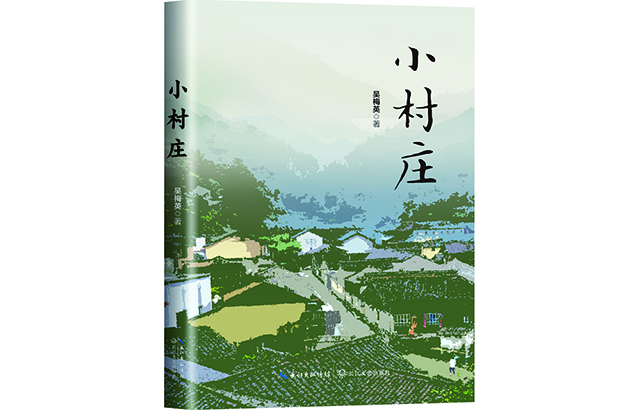
□高上兴
朝花夕拾是不少作家的写作策略。虽然70后吴梅英还远没有到夕拾的年龄,但经不住朝花带露,便有了这一本《小村庄》。
在这部散文集里,吴梅英时而出入青少年时的村庄,时而游走于壮年时的乡野,以极强的叙述耐心,回望童年和村庄,打捞那些沉潜在时光深处的记忆,并将它们重新安放妥帖。浙西南群山深处的小小村庄龙井,因而有了一份文学的标注。
一
吴梅英的龙井,位于丽水市龙泉市南部,与丽水市景宁、庆元两县交界。龙泉以青瓷、宝剑而闻名于世,龙井村却跟这两项技艺不沾边。它另有独门技艺:在过去,这里的村民以种菇为业,男人们冬天出门、春天回村,过着一种候鸟式的生活。
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构成了龙井村独特的文化背景,带来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吴梅英的散文,很准确地抓住了这种独特性,并将它呈现出来。在《拾榧及其他》中,吴梅英抓住了“接饼”这一独特习俗,写出了菇民平安回家后的欢乐和热烈。在菇民区,出远门的人,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带回来的饼分给左邻右舍。饼分大饼小饼,大饼由大人挨家挨户送出,小饼由孩子们上门接走。在接饼的习俗里,“我自然是这条河流的中心,被全村兴奋的浪潮抛起在最高点上”“当了主角的自豪感充溢着我的心田”。
然而,在这份欢乐和热烈的背后,还有被吴梅英隐藏掉的忧伤。稍稍了解香菇栽培史的人,都不难自己补上这隐藏在欢乐海洋底下的冰山。
这座冰山是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艰辛的创业史。过去,三县菇民常常远赴江西、福建、安徽伐山种菇。
当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再读到“吃了这家等下家,整个春天,龙井的孩子就这样等着爸爸们归来”时,那欢乐背后的一抹淡淡忧伤,也便随之而出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不多见的以香菇为题材的作品里,作者通常对外出的男人着墨较多,而对在家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则较少涉及或虽有涉及却不够细腻生动。吴梅英以其女性的细腻委婉,书写出了留守人的静默与煎熬。
“冬天是荒季,龙井男人都出门去了,只剩下老人、女人和小孩,在冷风里煎熬,饭桌前静默相对”(《雪落了一地》);“没有男人的老屋,夜晚显得格外幽深黑暗。……我们每晚都睡得很早,大人小孩全挤在一个房间,大家一进房间就赶紧闩上房门”(《老屋》)……这样的一些书写,应该说较好地补充了香菇题材的空白。
当然,在《小村庄》里,这样的笔墨只是露出了一鳞半爪。相信吴梅英在今后的写作里,还会有更多的拓展和深化。
二
再说回到龙井村。这个偏远的村子,有自己的方言,和龙泉话不大相同,这便给少年的“我”融入城市带来了局促。
乡音是农村人融入城市要去的第一道“疤痕”。如何对待这道“疤痕”?考验着作家。
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宝水》里,主人公地青萍也有这样一段试图把自己从乡土里拉出来的经历。在读《宝水》时,我同时也在读《小村庄》,两边跳来跳去读,一会儿穿梭于豫南的宝水村,一会儿又跋涉于浙西南的龙井村。虚虚实实、恍恍惚惚,感觉吴梅英就是地青萍。
乡土的强大拉力,总能以其独有温情和内在逻辑,重新把出走的少年揽入怀里。恩恩怨怨,得恩忘怨,乡土村庄是宽宽展展的,它不计较这些少年对自己的小小背叛。
当少年长大,当他们重新回家,乡土给予了他们最朴素的接纳。带着一点小小愧疚,站在壮年回望乡村、书写家乡,《小村庄》用了夕拾的笔调,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以成年的视角审视童年,以童年眼光打量世界,几乎也是朝花夕拾的标准范式了。但标准一致,也考验手艺。油盐少许、葱蒜若干,手力不同,味道各异。有的作品忆童年,手气重了,便显出陈旧味。手气轻了,便显油滑和轻浮。吴梅英的手气刚刚好。
在《动物之死》里,吴梅英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系列的动物:叫白蹄的猫、叫三百五的牛、叫欢欢的狗,还有不小心被“我”踩死的小鸡,这些生灵陪伴着“我”成长,又不断带给我心灵的颤动。踩死小鸡的“这一瞬间成了我生命至痛的起点。它将幼年的我撕裂,让其中的一部分永远停留在那个春天的天井里,永远不会长大,一直颤抖不已”。
也许,正是这一种颤抖,这一种永远停留的部分,成为指引我“回家”的灯火和星光。
三
吴梅英写散文,也写诗歌和小说。多种文体的训练,使她得以自由地在文字间呼吸。通读完《小村庄》,不难发现,在这些散文里,她实际上建构了一批形象。
且看一例。写母亲,这是难度很大的命题。滥俗、虚情、卖惨,等等,一个又一个陷阱摆在写作者的面前。吴梅英写《我的母亲》,也写母亲之死。这本是很沉痛的事,但吴梅英却忽然荡开一笔,将母亲生前的搞笑往事,夹在了母亲之死里。母亲上山砍柴,记错了柴放置之处,认为是别人把自己的柴偷走,也偷偷将“别人”的柴背回来,还“对我们姐妹眨眨眼,鬼鬼地笑着”。被父亲说她背的那捆柴就是自己的柴,母亲还不服气,硬说自己的柴更大捆。
母亲那狡黠、嘴硬的形象,瞬间就生动了起来。两相映照,生的欢乐,死的悲伤,交织共鸣,让人落泪。
此外,还有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当我们将《小村庄》里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我”捡拾、拼凑起来时,一些有趣的画面就出现了。“我大哭,却还不肯撤退。我躺了下来,躺到那冰冷的泥地上,不断蹬着一双腿”(《年味》);“坐在厨房漆黑的地面上,仰头声声哭喊”(《雪落了一地》);“我的家人烦我老张着嘴巴哭,给我取了外号叫‘水岸’”(《老屋》)。写上学的茫然:“我们以为抄写就是作业本身”,“每天本子发下来,一个大红X,我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默默盖上本子”(《六一》)。
类似的描述,如果不嫌麻烦,还可以再继续罗列一些。当我们把这些罗列出来,再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下,恐怕可以把“我”画得八九不离十。这实际上也是作者重新建构了一个自我的童年形象。
“我”是吴梅英吗?不知道。
“唯有共同的村庄,像一个水潭,容我们回返,短暂停留,又笑着再次出发。”
高上兴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