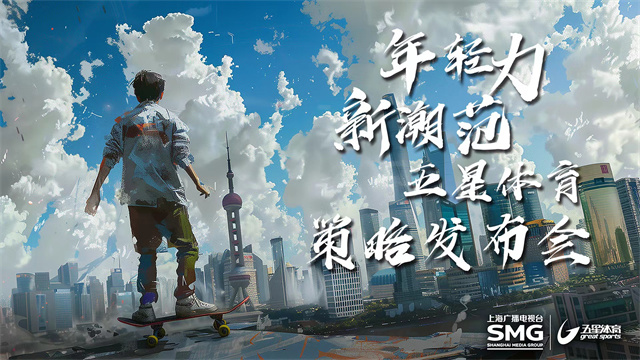Z世代文化报告|俞果:青年戏曲演员如何坚守?找到那个“热爱的点”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新近揭晓的白玉兰戏剧艺术奖让人记住了俞果。这位生于1996年的上海越剧院青年徐(玉兰)派女小生,凭借《舞台姐妹》中对邢月红的成功塑造,一举夺得白玉奖新人主角奖。然而,获奖并没有打乱俞果的戏曲生活,她依然在自己的戏曲世界里孜孜以求,不存在任何懈怠。她告诉青年报记者,她找到了让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那个“热爱的点”,就是观众的反馈和自己演好戏的一份使命。既然这一点没有改变,那什么也不会变。

◆ 感到很迷茫?找到坚持下去的那个“点” ◆
青年报:谈谈你的艺术经历吧。你是如何学的越剧?这里面有没有家族渊源?又是如何学的徐派小生?
俞果:我出生在杭州。杭州本身就是一个越音袅袅的城市。而带我的外公外婆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唱戏。记得小时候通常我在一旁的桌子上玩玩具,他们就在那里唱戏。有一天,他们教另外一个奶奶唱戏,反复教都没有学会,我在旁边突然唱出了这一句。大家都很吃惊,问我是怎么学会的,我说就是自己听会的。这时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在越剧上面有一点天分。
后来外公外婆就有意地培养我。他们买了很多越剧碟片,让我边看边学。我记得自己学的第一出戏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我家有个小九妹”。虽然里面是祝英台的唱腔,但她当时是女扮男装。我觉得自己日后唱女小生与这一唱段也挺有渊源的。外公外婆可能是看我唱得有模有样,给我订了一套小朋友的戏服。我就去参加各种比赛。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社区比赛,那时我人还没有舞台高,大人们就把我托举上台。唱的当然也是“我家有个小九妹”,唱完后评委可能还有点意犹未尽,就问我还会唱什么。我说还会唱《双珠凤·送花楼会》。那次比赛我还得了一个奖,获得一套床品四件套。从此以后,外公外婆更加想培养我这个兴趣爱好了。
后来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们举家搬到了上海。因为种种机缘巧合,上海越剧院的老师们关注到了我,我就到上海越剧院的“小花班”去学戏。这应该算是我学习越剧的启蒙之地。我们一家人那时都对越剧怀着浓郁的兴趣。我上“小花班”每周的周日是风雨无阻,除非我生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不然我外婆外公就会陪着我,早上练功,下午练唱练戏。可能是因为我“我家有个小九妹”这样的花旦戏唱得比较多,结果真正学唱戏的时候,就总是奶声奶气,捏着嗓子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嗓子是放不开的。老师没少为我想办法,让我躺在地上唱,让我拎着水桶边跑圆场边唱,就是为了让我把声音发出来。

青年报:和老一辈相比,现在青年人的生活和戏曲其实已经比较远了。你在学戏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克服的?
俞果:后来入读上海戏曲学校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那时“小花班”的老师们在考虑报考戏校的考生范围问题。外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接触大场面锻炼一下。结果没想到我很快就进入了复试。在复试的考场里就遇到了日后教我的著名徐派小生汪秀月老师。没想到最后在两三千人当中,我和二十几个小伙伴脱颖而出,考上了戏校。当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12岁,在年龄上算是破格录取。在学习了一年基础之后,汪老师就来教我们唱腔,他可能发现我的嗓音条件比较适合唱徐派,所以日后她就把我留在自己的戏组,开始精心传授我徐派艺术。
在正式学戏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其实还是很多的。起初就是我说的嗓音打不开的问题。后来又开始变嗓。变嗓比较多的是男生,女生变嗓蛮少数,我就是其中极个别的。记得有一天下午汪老师让我唱《红楼梦·金玉良缘》的第一句起腔。我唱了一个下午都没有唱上去,一到高音就破音,我遇到了变嗓。汪老师很着急,因为我要参加那一年的“小梅花奖”评选,所唱的《红楼梦·哭灵》里有很多高音。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反复练习,嘴巴就没有停过,情绪也变得很差。后来还是老师们教我一些真假声结合的技巧,才帮我度过了这一瓶颈期,最后还如愿评上了“小梅花”。
对我来说,这些其实还是很小的困难。我在学艺道路上,我一直都在寻找热爱艺术的那个点。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像老师您说的,我们这一辈跟前辈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前辈都是怀着一腔热情去从事这个职业,他们把这个职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热爱的那个点。这就是我们和老师们最大的差别所在,也是我在学艺过程中一直在苦苦找寻的。
没有找到这个点,就会感到很迷茫。尤其是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坚持的时候。我感到庆幸的是,戏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上海越剧院,当时越剧院特地为我们青年人成立了一个团,也就是现在的上越三团。在三团里,大家都是同龄人,有着一样经历,一样的困惑,大家也就一起去寻找答案。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古戏楼演《红楼梦》。在古戏楼版《红楼梦》里,我要把宝玉从小演到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压力很大。但是那次演出观众反馈很好,有观众看了后还会给我发微博的私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越剧,觉得越剧非常美,下一次有机会再来看我。这时有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一种是演完一个角色的一生的那种酣畅淋漓,一种就是“原来你的演出也可以给别人带来那么多快乐”。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找到了毕业之后一直以来的那个大难题的答案。从此以后,在练功房里苦练,我都特别情愿。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做好一点点,那观众就会看得到,会有人因为你的表演而喜欢上越剧,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找到了那个“热爱的点”。

◆ 戏曲是什么?演戏演人,演人演心 ◆
青年报:你的老师钱惠丽是徐玉兰大师的嫡传弟子,你是徐派艺术的传人。说说老师在给你教戏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
俞果:进入上海越剧院之后,就是钱惠丽老师带我了。目前我一共和她学了三出大戏《红楼梦》《西厢记》和《舞台姐妹》。有一次学《西厢记》,我看到钱老师1980年代的一个视频,发现那时剧中张君瑞的出场和现在不一样,他是快步走到台中,突然打开扇子一个亮相,现在则是徐徐展开扇子,然后一个小亮相。我当时觉得老版本的亮相好帅。然后就和钱老师谈起这件事。没想到钱老师就跟我说,如果你觉得那个亮相很帅,那你要不要改成老版本。我想了一会儿说,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样不符合人物塑造。钱老师听了很欣慰,她说,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来问你一下。那一刻我突然体悟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她就是来看看你对这个人物的见解是否跟她一样。在拍戏的过程中,她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先按照我这么做,如果你能想到比我这个更好的,我们就用你的。她不允许学生一直模仿她,她希望学生自己能够创造东西。
很多人问我,钱老师是不是很严厉的老师?我说其实不是,她严肃的时候,其实是她在思考之中。你问她一个问题,她不会马上回答你,她会去想,我要怎么样把你们每一个学生的所长都发挥出来,而不仅仅是模仿她而已。我觉得这是老师很难能可贵的一点。她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次我去参加“越美中华”的评选,在复试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没有自信,她就想尽办法给我打气,最后她还对我说,“你到底担心什么?难道你觉得这个比赛你比不上,我就不要你了吗?”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平时不会这么跟你说话的,但是在某一刻,她会突然给你一些由衷的鼓励。

青年报:前面说到,现在的青年人与传统戏曲其实是有天生的距离的。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戏曲氛围,让自己保持对戏曲的敏锐度?
俞果:我们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会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台上开关门的动作,那就可能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我们台上走几步路,那就是几百公里,我们袖子一遮,就知道那里飘过来了雨。这些东西都蕴含在我们的四功五法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平时的排演中不断练习。另外,我觉得一个演员也好,一个作家也好,任何跟艺术有关的行业的从业者,他一定都对生活保持着一颗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可以帮助你去捕捉到生活中很多细小的东西。
相对于昆曲来说,我们越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越剧表演的部分吸取了话剧等形式,所以对我们的表演来说,程式化的东西是有的,但它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挖掘人物内心。就拿我这次在《舞台姐妹》中演的邢月红来说,她在舞台上是女小生演员,我也是女小生演员,我感觉和她距离很近,但突然一瞬间,我又觉得我们离得好远,因为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而我是生活在2024年的。其实在饰演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困扰,但是越剧前辈刘觉老师在他自传里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启示。刘觉老师说,戏曲就是“演戏演人,演人演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一直去挖掘人物的内心,去更贴近人物。
在生活中我一直让自己保持着这一份对戏曲的敏锐。比如我看剧,看到一个人表演得很好,我就会暂停,然后想一想如果是我演,我会怎么演,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会突然唱起来,这就是一个戏曲演员的生活,因为确实应该曲不离口。我对生活一直抱着好奇心。有时候遇到一件事就像戏里演的一样,我就会想,如果把它写成剧本要怎么写。

◆ 青年人的使命在哪里?首要任务是传承经典 ◆
青年报:你这次凭借《舞台姐妹》获得了白玉兰奖新人奖。和你过去排演的剧目相比,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俞果:《舞台姐妹》里我演的邢月红,在舞台上是女小生,但是在生活中却是小女生。这种切换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老师经常问我,你不就是个女孩子吗,怎么觉得你在反串?我回答,我不知道生活中女生的形态要怎么去表现。在舞台上,我经常扮演传统戏曲中的男性角色,所以当我出现时,观众会默认我扮演的是一个男性角色。因此,当我要同时展现小女生形象时,挑战就很大了。
在演出的时候,我一开始总是将邢月红和贾宝玉混淆,因为两者年龄相仿,表现手法也偏向于可爱。但其实两人又截然不同,宝玉是古装戏里的叛逆小男生,而月红是一个从小受保护的小女生,这种表演上分寸感需要我去拿捏。随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从小女生自然过渡到成熟女性?因为我是演了邢月红的一生,小女生我还会演,但是成熟女性我就有点掌握不好,毕竟缺乏生活体验的支撑。那段时间排练我很痛苦,因为我总是演得很悲情,但老师说这时候没有悲伤,只有失落。
我们这部作品能够获得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团队、对我们越剧院复排经典作品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青年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白玉兰奖,会不会因为获奖而影响你平时的训练和排演生活?你觉得这次得奖对你最大的意义是在哪里?
俞果:在颁奖典礼结束后,我立即投入到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中。在这段时间里,我偶遇了院长,他询问我对获奖的感受,我坦诚地表示尚未习惯这份荣耀。实际上,我认为自己的转变开始于饰演邢月红之后,我选择专注于对角色的诠释以及展现我作为越剧演员的责任。获奖后,我的内心反而更加忐忑,期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因为奖项为我带来了更多关注与期望。这种被注视的感觉让我渴望展现最佳状态。
此后,我更加不敢懈怠每一次演出。记得在6月2日浦东的展演前,我在家中苦练唱功后仍感不足,便独自留在排练厅,从中午到傍晚。我反复观看前辈的视频,深受触动,泪眼婆娑中自我演绎,又通过老师的表演寻找新的情感共鸣,如此循环往复,内心充满了收获与充实。这种从经典中汲取新知的体验,是我所珍视的良性循环,也是我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如今,面对每场演出,我都全力以赴,生怕辜负观众的期望,尽管这些期望的具体内容我难以把握。令人欣慰的是,有观众在观看演出后反馈,认为我的表演更加细腻生动,这无疑是对我努力的最大肯定。我深知,人物的鲜活离不开时间的沉淀与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角色的深入思考。

青年报:青年演员肩负着传承戏曲、发展戏曲的重任。但是就如前面所言,环境已经不同了,你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戏曲演员,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体现时代感?
俞果:我倾向于将“青年演员”这一身份细分为“青年”与“演员”两部分来探讨。作为当代青年,我们理应心怀文化自信,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形态保持自豪感,尤其对中国文化更应如此,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身处上海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我们拥有诸多机会接触国际艺术前沿,比如通过国际艺术节等平台,无需远行即可领略众多优秀作品。各种展览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这是上海青年独有的优势。
谈及演员身份,文化自信同样不可或缺。当前,国家对文化振兴给予高度重视与支持,我们的创作环境相较于前辈艺术家们已显著改善。因此,作为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们更应专注于戏剧本身,深入钻研。上海越剧院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历代艺术家在此辛勤耕耘,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源和学习范本。
作为新一代青年演员,我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经典。在目前阶段,创新尚显遥远,上海越剧院这座艺术宝库中的经典剧目,正是我们汲取营养、打牢基础的源泉。通过精心排演这些经典剧目,我们方能实现真正的守正。同时,我坚信创新应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唯有基础扎实,我们的创新才能不逾矩、不偏离,从而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为大众所接受的作品。
我认为,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作为青年戏曲传承者,我们应摒弃杂念,专注于提升自我,认真履行戏曲演员的职责,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