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窗外鸟叫了——散文集《云边路》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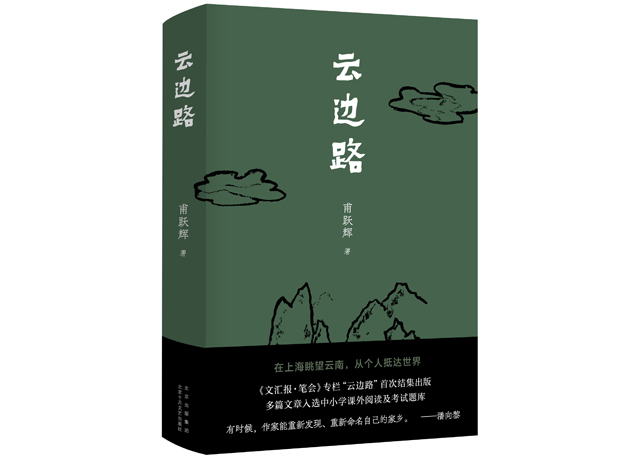
□甫跃辉
这一系列短文原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中。之所以会写,和《文汇报》时任特聘首席编辑潘向黎有绝大关系。记得是2014年,潘姐和我约稿,然而,我并没适合“笔会”的文章。我写的主要是小说,除了偶尔写点儿创作谈之类的,几乎没写过散文。
两年后,小说集《安娜的火车》出版时,我写了《和我有关的世界——谈谈我的最新小说集<安娜的火车>》。问潘姐这样的稿子能不能用。不久,潘姐回复说:“当然能。”这成了我发表在“笔会”的第一篇散文,时为2016年1月20日;几个月后,心血来潮写了《上山拾菌子》,成为我发表在“笔会”的第二篇散文,时为2016年7月28日;接着,又发了《奶奶的茶园》。后两篇散文都是写故乡施甸的。我想,要不写一系列这一主题的短文吧?
“笔会”编辑部几位老师商量后,让我在“笔会”开个专栏,大概一月一篇。我非“名家”,且没写过几篇散文。“笔会”竟能让我开专栏,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信任——犹记得刚发表专栏第一篇《高黎贡》时,周毅老师发来微信,说“这篇震住我了”,让我惊喜又惶恐。
去年,周毅老师遽然仙去;从《在工地》开始,我的责编换成舒明老师。一个专栏,竟见证了外部这么多人事变迁,不由得让人感慨。
回想当初,想过好几个专栏题目,最后选定的是“云边路”。
云边路,是依稀的来处,也是渺远的去处。若细抠字眼,最初的想法是,“云”即云南,“边”即边疆,“路”呢?自然是指我在施甸这云南边疆小县度过的十九年。但我想把“云边路”的写作领地大致圈定在保山,而不仅仅是施甸。保山下辖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腾冲市和市政府所在地隆阳区。保山不仅有高黎贡,还有松山、怒江、澜沧江……这些高山大河,是被我从意识深处当作“故乡”的地方。
之前,我在几家报纸开过专栏,没有哪个专栏写了超过三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话还真不错。潘姐说,她是个好编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自己都没想到,“云边路”这专栏,竟然很快就写出了不止三十篇。那些注定跟随一辈子的记忆,在我写作十多年后,闪耀着簇新的光亮,自己打开闸门,奔涌至眼前。
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念写这部长篇,已是2011年,最初的动笔,也已经远至七八年前。然而,第一稿废了,第二稿废了,现在,我所写的是完全推倒重来的第三稿。每天打开电脑,点开文档,盯着,直到十点,十二点,两点……现在是三点十六分,窗外鸟叫了。夜幕被一粒粒鸟鸣射出千疮百孔。又是新的一天,待中午起床,打开电脑,继续盯着。新的一天!我仍然没写出一个字。为什么写不出一个字?!思绪像生锈的螺丝,被死死地拧在了最末的一个字眼上,没法往下挪动一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极度沮丧,沮丧后又一再涌起希望,希望过后是更深的沮丧。我想,我怕是永远写不完这部长篇了……还好同时在写作“云边路”,让我能够确信,我拥有的文字江河并没有枯竭。
不过,“云边路”的写作和小说很不一样,材料是直接从现实记忆里捡拾来的。写了四五篇后,新的困惑产生了:这样书写究竟有多少价值?实在有太多人在写记忆、写乡村、写亲人、写习俗了。我所写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伴随着困惑,“云边路”一篇又一篇地持续产出。
自2017年4月24日《高黎贡》发表,到如今,“云边路”系列已经在“笔会”发表三十多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学报》《广州文艺》《大益文学》《温润保山》等报刊也零散发表了二十多篇。其中,《温润保山》是保山的内刊,虽为内刊,印制却极为精美大气。主持刊物的蒋开磊兄,于2017年第1期开始,在刊物上持续刊发“云边路”系列,让我和故乡的人们多了一份文学情谊。转眼之间,“云边路”就要从专栏变成一本书了,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而我的计划是,即便结集出书了,“云边路”专栏仍会继续,甚至才刚刚开始:一个世界正渐渐显形。
我渐渐明了,要在“云边路”的世界里建构怎样一个“文学世界”:和我的记忆有关,和我的当下有关,还和保山的历史与现实有关。个人经验和地方历史交织,“云边路”里的保山才能成为一个细微而宏大、复杂而立体的文学地理。而最终,“云边路”不应该仅仅是指向一个人或一个地方,而应当指向生命和世界。
作为“附录”的《我和我的村庄》,是我刚刚开始写作时写下的二三十篇更短的短文。编订书稿时,忽然想起这组文字,意识到,这是“云边路”的源头。故乡的山川草木,是早早就召唤过我的。然而,我走到别的路上去了。如今,它们终以新的面目呈现。
希望我的文字,能够照亮故乡僻远的高山大河和悠远的蛮荒岁月,也照亮自己的生命。
(散文集《云边路》,甫跃辉著,北京十月文艺2020年12月出版。甫跃辉: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五陵少年》《万重山》等。)
甫跃辉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