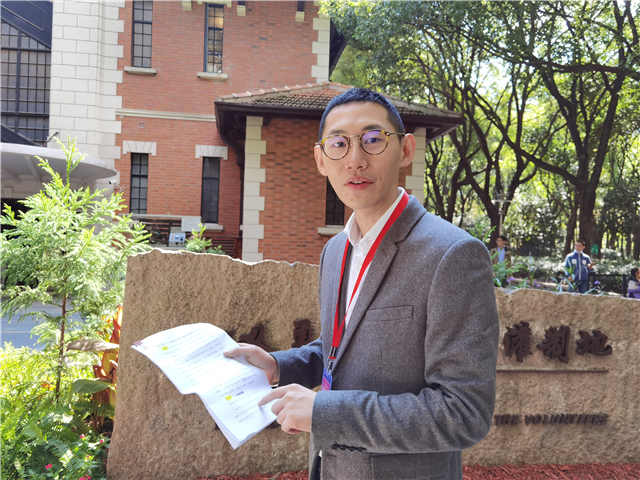上海访谈|我性格中的坚毅品格源于我的热爱,戏剧天生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

在孟冰看来,剧作家重要的不是出身,不是众星捧月,而是一种对于戏剧最执着的热爱。有了这份热爱,剧作家才会在困难面前变得坚毅,才可能与他的生命、他的热血相融通,才可能写得出堪称伟大,能够引发全民族共同思考的作品来。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孟冰也对青年一代编剧提出了希望,不要过于职业化,把编剧仅仅看成是一份营生,“这样做是做不好的,因为他没有生命的感受,没有鲜血的流动,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能会想到放弃”。
青年报记者 郦亮
1 今天年轻一代的编剧可能更职业化,他们觉得这是营生,就是为了挣钱。这样做是做不好的,因为他没有生命的感受,没有鲜血的流动。
青年报:您是怎么走上编剧这条道路的?据说当年您带着作品向北京人艺于是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还让您别当编剧,因为这个职业太苦了。是什么促使您坚持走下去,并且在编剧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孟冰: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是有选择、有规划的,我们那时不是这样的。我十四岁就考进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当时我们的老团长魏敏同志就定下一个规矩:新人来到部队文工团首先要从演战士开始,但没当过兵,不熟悉战士,又怎么能演战士呢?所以进文工团的年轻人凡是没有当过兵的,都要送到部队去体验生活。于是,我刚到文工团不久就被送到野战部队去锻炼。基层部队需要文化生活,我们又是从文工团下来的,所以很自然的人家会要求我们进行文艺创作和表演。
我们的演出基本上都是自编自演,我那时就会写对口词和枪杆诗。我们大概七八个年轻人,自己写自己演,有时一晚上能演两三个小时的节目。演完了之后,第二天营长来了,他听说昨天节目演得很好,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问我们今晚再演一下可以不可以?我们就经常这样演出,节目演完了之后还会有一个40多分钟的独幕剧。那应该是我写的第一个大一点的作品吧。
青年报:那个独幕剧叫什么名字?
孟冰:叫《打不打》。写的就是我们班自己发生的事情。当时部队正在进行打靶训练,轮到我们班打靶那天赶上下雪了。班里有的同志提出来天气不好会影响我们班的成绩,应该换一天再打;也有人提出来不能换,理由是真的打起仗怎么办?我写的这个独幕剧就是讨论打靶是“练为战”还是“练为看”。因为我是以班上几个熟悉的战士为原型进行创作的,然后又模仿着这几个人去演,于是,演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全连笑得前仰后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特接地气。演完之后,连长就问全连战士:他们演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于是,又演一遍……第二天一早,营长骑着大白马来了,他一见我就问,听说你们昨天节目演得很好,我还没有看到,今天晚上再演一遍好不好?于是,又是一个“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等节目演完了之后,营长当即宣布:明天早上全营不出操!
那个时候我们深深体会到文艺工作确实能提升部队的战斗力。那种令战士群情振奋的作品,确实能够发挥鼓舞士气的作用。
青年报:我注意到您当年入战友话剧团起先是演员,后来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转向编剧?
孟冰:我开始是学表演的,那为什么后来慢慢往编剧上转了呢?主要原因就是个人爱好吧。我平时就喜欢读剧本,也喜欢文学,那时自己就开始写日记,看了电影后会写个影评啥的,过年过节读了点诗后会突发奇想诌两句“歪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当演员时外形条件不是很好,比如说身材不够高大,体形不够魁梧,关键是当时处于变声期,嗓子拖泥带水的也不宏亮。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担任主角,只能演匪兵甲乙、路人甲乙之类。而且那时文工团也有淘汰率。虽然我当时也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舞台工作和勤杂工作,但是总有人说我:你很危险,说不定明年转业就轮到你了。
青年报:但是您毕竟不是编剧科班出身,在事业转型的过程中一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孟冰:那时,我可以说真是压力山大呀。所以就很刻苦努力地向编剧方向转。但是转行做编剧哪有那么容易?更何况我不是科班出身,完全是土生土长。记得那时候写了剧本,就去请教老同志,凭着一股子韧劲,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常常拽住老同志就给人家读剧本,让人家提意见。修改后不厌其烦地再去找人家,弄得人家没有办法,被缠得够呛。但慢慢地在成长和进步中被大家认可,最后一致认为小孟同志很努力、很刻苦,在写作上还有那么一点灵气和天赋,是那个“虫”。我能有今天,应该感谢老同志们非常爱才,他们非常高兴能有年轻人如此执着地热爱创作,那时的我受到了老同志们刻意的保护和培养。
青年报:听说您曾经差一点被转业,是老同志的保护让您留在了文工团,有这回事吗?
孟冰:在这方面有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事例。当时已经到军区文化部当副部长的魏敏同志即将离休,我那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进修,正赶上部队文工团整编,需要精简人员。当时的团领导确定让我转业,而且名单已经报到上级领导机关了。魏敏同志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去找了我们部队的高层首长,他问部队首长:“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是一个专家?”首长说:“当然承认了,您是我们战友话剧团25年的老团长,很多人都是您培养出来的。”魏敏同志接着说:“如果你们承认我是专家,我就告诉你,我认定了小孟是个人才。你们现在让他转业不行,你把他交给我,我带着他去写剧本。我保证一两年之内写出在全国得大奖的剧本。我可以立军令状,如果不行,我离休他滚蛋!”我终于留下来了,而且就一直跟着魏敏同志学习进行剧本创作,一年之后,我们终于写出了《红白喜事》。这是我的成名之作,从此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青年报:于是之老先生也对您说,编剧苦得不是人干的。在您的编剧生涯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孟冰:虽然当编剧很辛苦,也很艰难,但我却从没想过放弃。这可能与我性格当中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有关吧。其二,这也源于对自己所选择的一件事情的热爱程度和执着程度。就我而言,我对编剧的情感远远超过了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没有达到这种超乎常人的痴迷状态,就不会凝聚这样的力量,就不会迸发如此的激情,就不会将自己整个身心完全投入进去,忘我地徜徉其中,甚至有时会带有“自虐性”了。怎么理解这个词?先说客观环境,周边人们对你理解不理解?支持不支持?你有没有条件来从事这项工作?你这样做,别人怎么看?除了客观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心理的把握,也就是能不能够达到这种我刚才所说有一点极端的词句“自虐性”,也就是对自己非常严酷。看书、写作……这一切都是业余时间,你的正常时间是参加团里的各项工作,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工作,而剩下不多的时间,排除一切娱乐活动,而且每天读书或写作要到深夜,还要坚持数年……直到今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说现在我已经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先看我自己写的剧本,这是从不间断的。现在很多人写完了剧本自己都不会再看,他对自己的作品都不热爱,他甚至都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再去看,这个作品怎么可能会是好作品?怎么可能成为佳作?因此,自己一定要热爱自己的作品,呵护自己的作品,尊重自己的创作。每天去看看它,哪怕只修改一个标点符号,都会让它臻于完美。

2 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年轻人思想上的进步,也是他们认知上的进步。
青年报:这种带着“自虐性”的工作,有没有让您厌倦?
孟冰:有过一些很困难的阶段,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很愉快的。也有痛苦的时候,比如修改的时候意见不统一。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也会有不开心啊,甚至有的时候也会生气,年轻的时候也发脾气。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愉快。
所以对年轻一代的剧作家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作为我们这些老一代如果要和他们进行交流的话,我恐怕要跟他们谈的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一代的编剧可能更职业化,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营生手段,可能就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交车贷,为了交房贷。我觉得这样做编剧是做不好的,因为没有生命的感受,没有生命的冲动,或者说生命的冲动不是精神追求,没有鲜血的流动,没有发自肺腑的热爱,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能会想到放弃。
青年报:您提出过一种“政论体话剧”的理论。《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开天辟地》《谁主沉浮》《寻找李大钊》都属于这类话剧。究竟什么是“政论体话剧”?为什么现在需要这类“政论体话剧”?您为什么偏爱这种形式?
孟冰:我在中国是比较早做“政论体话剧”的。所谓“政论体话剧”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前苏联有个著名的剧作家叫沙特罗夫,他有几部非常有名的剧作,像《前进!前进!前进!》《我们一定胜利》《良心专政》等。他的戏剧里有列宁的形象,但并不追求外形上的相似。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叫作“列宁的思想即列宁的形象”。就是不强调演员表演列宁的外形,而是注重表现他的思想、他的观点。还有,过去我们一直在讲戏剧的冲突主要是指“舞台行动(行为、动作)”,但是“政论体话剧”在这方面有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就是允许政治观点在戏剧中辩论,允许剧中人(主要是指领袖人物)直接讲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且,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包括引用社论、新闻报道、图片、影片、资料、史料……厦门大学的陈世雄教授有这方面的专著,值得学习。这种方法为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我在写《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时,毛泽东有大段的台词,无论是他讲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还是讲述他自己的身世经历,讲述他和杨开慧的情感,特别是讲述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些是不需要完全与剧情贴切在一起的。
青年报:这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观众尤其是一些青年观众对于政治题材、红色题材的舞台和影视作品很关心。很多都成为爆款。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等。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否意味着观众的一种觉醒?
孟冰:我也注意到这个情况,就是现在青年人对红色题材、政治题材的文艺作品很感兴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说明几个问题。第一,经过这些年的宣传,特别是今年又赶上建党百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契机,使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我们的时代,关注我们的历史,关注我们今天时代的成因。这是时代的进步,是我们年轻人思想上的进步,也是他们认知上的进步。第二,这也说明我们的红色题材的作品这些年在创作上更加成熟了。比如说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决战》,我觉得都非常好。它们不仅仅完成了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叙述,重要的是它们也能够很生动地刻画重要的领袖人物和历史人物,能够很人性化地、很真实地把他们放在大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当中去表现,不是故意地拔高,也不是故意地去贬低。就说《觉醒年代》中李大钊跟陈独秀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争论,包括陈独秀后来跟胡适他们怎样进行争论,在剧中都详细地描述。中国革命道理的探索不是说一天两天读一两本书,头脑一发热,就搞起中国革命,就找到中国之路了,它是个很艰难的过程。能够从关注大时代和其中人物的命运中去感受历史风云,说明我们在红色题材的创作中确实成熟了。
青年报:您的编剧作品以原创为主,但也有一两部例外,比如不久前到上海来演过的陕西人艺的《白鹿原》就是改编自陈忠实的原著小说。这部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话剧舞台的经典之作。特别想听您讲创作《白鹿原》话剧的过程。原创与改编的最大不同主要体现在哪里?
孟冰:先说一下话剧版《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吧。当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林兆华先生找的我,问我能不能改编小说《白鹿原》,因为当时小说改编权是北京人艺最先拿到的。但是找我的时候,版权期只剩一年时间了。当时我也不敢贸然接这个事。我就对林兆华说,我还是再看一遍小说再回答你吧。等我又重新看完小说以后,觉得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太复杂了,我又去和林大导商量,我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做?能不能不做,因为确实难度很大。林兆华想了想坚定地说,还是要做。我说你既然决定要做,我就下决心做,不管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在创作《白鹿原》剧本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到这部小说中了,一进去就是9个月的时间。9个月后我拿了初稿,去找林大导,他看到我的初稿后愣住了。因为我捧着一大摞稿纸站在他面前。搞话剧的都知道,我们的前辈曹禺、吴祖光、陈白尘,他们的本子动不动五六万字,甚至10万字,吴祖光先生的剧本有20万字。但是现在的编剧,一个本子写到3万字就要演出三个多小时了。我给林兆华的一摞稿纸起码有100万字。这些文字都是我做的功课,包括:小说情节结构的分析、小说中的人物行动线,还有对可以进入戏剧的小说情节、语言、细节的提取等等,另外还有我和陈忠实老师的谈话纪要。当时,林兆华就对身边剧院的同志说,你们看到了吗,今天还有这样写剧本的。
青年报:后来这个戏排得还顺利吗?
孟冰:北京人艺在排练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关于方言的使用问题。我当时就跟林大导争论过,我就不同意他们使用方言。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陕西方言说得不标准,这样反而影响效果,除非说得非常地道。后来陕西人艺来演《白鹿原》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家方言说得非常好,于是,它成为艺术特色!北京人艺演了几年以后,因为他们的经典剧目太多了,每年演不过来,有时《白鹿原》就不一定能放到演出日程上去。正好北京人艺的合同授权时间也到了,这时候陕西人艺就想到要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回家”。听说当时陕西也有编剧改过这部作品,最后是陈忠实先生表态,你们(指陕西人艺)还是用孟冰的那个本子吧。所以,后来陕西人艺在做宣传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作“陈忠实先生最满意的版本”,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

3 戏剧这种样式天生具有一种“当众思考”的品质,因此也一定有社会责任。这不是我们强加给戏剧的,而是这种艺术形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携带着对社会的认知、对民众的认知,以及它一定集合着民众的共识。
青年报:您特别强调一个剧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为什么?您说“我有这样一种信念,无论是对美好的赞扬,还是对丑陋的批判和抨击,都是出于一种真心的爱护和提醒,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体制、思想领域的进步”,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孟冰: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的“剧院是一个民族当众进行思考的场所”。我个人认为,戏剧这种样式天生具有一种“当众思考”的品质,因此也一定有社会责任。这不是我们强加给戏剧的,而是这种艺术形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携带着对社会的认知、对民众的认知,以及它一定集合着民众的共识。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绘画和音乐不同,绘画和音乐是艺术家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和别人讨论。但是戏剧在剧作家表达完之后需要观众的参与,可以有掌声、笑声,甚至谩骂和质疑。过去在解放区,我们很多剧团演出《白毛女》的时候,战士看得很悲愤,举枪就要打黄世仁。听说在欧洲《奥赛罗》演出时,也出现过观众举枪把演员打死的事情。话剧从一百一十年前传入中国时,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民族的重任,在抗日战争中,话剧号召大家不要当亡国奴,动员民众抵抗侵略者。我觉得中国的话剧总是与中国的历史和特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起到了一种鼓舞、启发、动员、感召的作用。
青年报:过去的老一辈剧作家在践行使命和担当中提供了榜样,您觉得现在青年一代的编剧做得怎么样?
孟冰:我注意到现在青年编剧的作品还是很多的。从一些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可以感受到青年编剧们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类命运包括青年人自身命运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种种思考。比如上海改编的《繁花》,我觉得很好,还有上海的编剧喻荣军,前些年我从《老大》那部作品开始就关注他,我觉得他的那种沉淀,他对社会的那种认知,已经在发生一种很内在的、很深刻的变化。还有江苏擅长写戏曲的罗周、广东的陈新华、北京的冯必烈等一些青年编剧,已经有许多优秀作品出现。年轻戏剧人的作品有时虽然可能轻松多一点或者娱乐多一点,我觉得他们是在有意地摆脱戏剧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一些伤害。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意夸大戏剧的某种夸张的、变形的、荒诞的表现形态。这种探索我觉得无可厚非,也都是有意义的。
青年报:说说编剧这个行业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轻编剧而重演员的情况很普遍,演员的报酬占了成本的大多数,而编剧普遍收入很低。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编剧在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
孟冰:受历史的影响,文化人总是不愿意被宣传,认为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有一段时间也看不起文化人,觉得你是“臭老九”。这些方方面面的综合作用,就使得有一段时间文化得不到尊重,有文化的人得不到尊重。
现在当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逐渐在正本清源,逐渐在梳理混沌,重新捋顺人们的基本的观念和基本思想认知。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普及的呼吁,现在在教育上的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在传媒、在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在娱乐界的这样一种纠正的风气,都使得一种健康的、正直的、透明的、清亮的文化传统开始回归。这样的话,我觉得它自然而然地会使得剧本创作的人意识到“编剧”称呼和“剧作家”这个称呼是不一样的。影视剧当中你可以叫作“编剧”,但你也可以成为剧作家,成为艺术家,这个得你自己用作品去说话。我觉得写剧本的人始终要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从业者,而且是一个能够影响社会的人。每个人的生命体量是不一样的,只要它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完美的绽放,能够经历一个完美的过程,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就没有白白地浪费。
· 中国戏剧大家系列访谈之三十六 ·
孟冰,一级编剧,原总政话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
主要作品有话剧《红白喜事》《绿荫里的红塑料桶》《黄土谣》《白鹿原》《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寻找李大钊》《谁主沉浮》《伏生》《这是最后的斗争》《公民》《平凡的世界》,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和现代京剧《西安事变》等。至今共创作戏剧作品70部,其中上演作品54部。这些作品中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的有6部,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有15部(其中戏剧作品12部,电视剧作品3部),获文华大奖的有6部,获文华剧目奖的有7部,获文华编剧奖的有5部,获曹禺剧本奖的有6部,共获全国及军队重大奖项85个。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文化部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五次荣立二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系列访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合办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