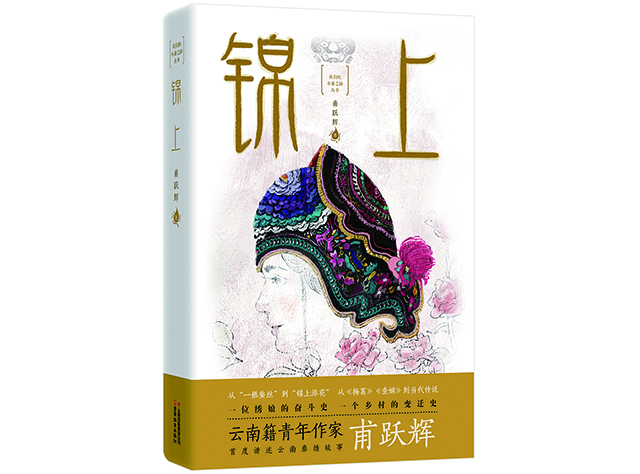荐读|穿越时空的枷锁——读甫跃辉长篇小说《锦上》
□高毅月
王安忆小说以细密繁复的细节描写著称,师从王安忆的甫跃辉同样注重细节描写。不同的是,其细节描摹几乎不支撑或服务于故事性。相较于呈现有发展、有高潮的连贯情节,甫氏小说要抽象得多,接近隐喻,恰恰不以好读性取胜。《动物园》《饲鼠》《巨象》都是此类作品,包罗现代性思考、精神寓言、社会想象,甚至福柯意义的“规训与惩罚”。面世不久的《锦上》也不例外,小说分十章,每章讲述一个故事,几个故事之间关系不多。当然,各章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否则就不是一部小说了。就此而言,《锦上》以互文结构弥补自身的离散和分裂。
互文性概念的产生和接受经历了一段矛盾的发展,比如被看作“文本的对话现象”“一个周而复始的文本套式”“文本的一种修辞学”,模糊的界定导致灵活地使用语境。事实上,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词、对话、小说》首次使用这个术语时,指的是这样一种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也就是文本之间引用、转变、参考、派生的关系。其中引用(指“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的出现”的情况),被热奈特认为是构成互文性的最直白形式,与抄袭、暗示、借用等形式不同,引用部分诚实地加了引号。引用史诗显然是《锦上》的鲜明表征,小说引用的史诗材料与正文构成怎样的互文关系?生成怎样的表达效果?以及阅读体验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难免带有主观性。这也正是互文性的特征,萨莫瓦约说:“对所有互文现象的解读——所有互文现象在文中达到的效果——势必包含了主观性。”
笔者认为,主观性存在却不构成统治。客观来说,引用在形式上增大了《锦上》的散态,在内容上又补偿了这种分散性。如第一章“源起”,卷首引用彝绣故事《蚕丝》,结尾标注“选自彝族长篇史诗《梅葛》,郭思九等搜集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使用具有标识性的字体,这样造成与正文的不连续性。蒂费纳·萨莫瓦约认为这种情况下,分离大于吸纳。事实上,如此一来,的确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古典与现实)、两种不同体式的话语(歌谣体和白话体),不过正文仍然是由此衍生的。在“源起”统摄下,作为彝绣源头的蚕丝故事和主人公阿各初生的故事,本质上是一样的,两条线索分别展开,最终回到起源主题。这是一个环形拓补结构,两者被归拢于一个框架,一个中心。
除了结构,内容也并非毫无联系。《蚕丝》是彝族史诗《梅葛》里面远古时期的养蚕故事:“蚕种找着了,哪个抱蚕子?汉家姑娘抱蚕子。三年闰一月,一年打两春;打春后三天,桑树发出来,蚕二钻出来。”描述了一幅古朴的桑蚕景象。正文则写了阿各家主要依靠养蚕、卖蚕茧维持生活。这里有农耕文明的记忆。世界早已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大彝山的生产方式却保留了祖先传统。两者的组合很容易让人想到时间在大彝山的凝滞,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历史在那里似乎是失效的,几千年来,人们几乎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除此之外,《蚕丝》独特的叙事节奏、韵律、语言也塑造着小说的美学风格和文化属性。也就是说,互文性并不是机械的,在这个有机环境中,一切因素都是生成意义的。
有时候,不妨把引文和正文视为彼此的外延。第四章卷首引文“诸葛南征”,讲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途中重视南地文化习俗,派孟获夫人到蜀国学习汉族刺绣工艺,将蜀绣技艺传授给彝人女子,孟获夫人被称为“刺绣女神”。正文则讲了上海女孩郁青兰随父母到楚雄农场支边,对彝绣文化产生兴趣,大学毕业后到楚雄参加文化工作的故事。南下或者北上,不论以什么方式,都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重组。在这里,“南征”或者“支边”都不构成对象,而是作为背景,是中国南北文化对话的形构。外来文化不是入侵,而是调和融摄,不是对峙,而是互为张力。彝绣吸纳了蜀汉元素,也与上海流行文化交叉。郁青兰可以说是当代意义的彝绣女神,与鲁迅对神话人物的戏拟不同,她是孟获夫人的延续而非解构。
实际上,就《锦上》的创作动机而言,大概可以归纳为民间文艺开掘,少数民族文化与汉语主流文化交融,中国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演变等关键词。文化关系的具象化不仅表现为郁青兰、孟获夫人与彝绣的交集,阿各与郁青兰的相遇同样颇具寓意。她们“一个从头到脚穿着一身绣花衣服,一个牛仔裤搭配白衬衫”,这实质上是两种文化风格,一个开放、直白、张扬,充满现代性;一个隆重、繁复、讲寓意,保持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性格。两者都被对方深深吸引。不过,在阿各眼里,上海多少具有“优越性”,她“到上海去”的意志屡遭失败。直到小说结尾,随着彝绣事业的成功,才去除了这种疏离感和等级机制,文化区隔被打破。甫跃辉的深刻性在于,文化交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小说不仅塑造郁青兰南下楚雄,楚雄阿各不仅去上海参展,还要带着彝绣艺术走向世界舞台。这也是小说借人物之口展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文化意识和胸襟。总的来说,不论是孟获夫人、郁青兰还是阿各,都被当作文化使者的象征。穿越时空的枷锁,几个故事完成了文化交融主题的多重表述。
洛朗·坚尼在《形式的战略》中写道:“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型地阅读文本。” 互文性永远激发读者更多的想象和知识,这是毋庸置疑的。《锦上》的引文要求读者要么查阅《查姆》《梅葛》等史诗原文,进入新鲜、陌生的史诗天地。要么本身就具有相关的知识和记忆,从而进一步寻找寓意或补充材料。这种满足读者参与性和创造性的阅读体验,不仅仅来自引用,文本内部也多有提示。有时是反复出现的意象,比如“上海”“飞机”“马樱花”意象;有时是或明或暗的线索,比如秀给独和黑彝老人,面对丈夫出征不归的命运,两人有很多共同点。甚至不妨是文字锤炼:“她坐在小板凳上挺了挺身子,伸出手在地面摸索,然后碰到一根松柴。”“碰”字准确描述“看不见”的情形,读者很可以从中推测老妇的盲人身份;有时是暗示,第三章卷首引文“种棉”,讲彝族歇索祖先的开荒种棉史。正文再次提示阿奶唱的章节是“麻和棉”,从“种麻”唱到“种棉”,倒像是专为阿各要做的事情唱的,而阿各也在心里愿意把这当作一个预言。读者很容易想到阿各到深山收集彝绣,只身打开彝绣市场几乎是在重走歇索祖先的开荒史,重复祖先征服荒原的经验和精神。
如此说来,《锦上》的互文结构并非偶然,恐怕是作者有意选择的创作形式。萨莫瓦约在讨论互文性时不得不首先讨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他显然认为对话主义正是互文性前身。巴赫金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了复调形式,证实了对话主义。甫跃辉受陀氏影响极大,写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孩子》,不仅深入研究过陀氏小说的儿童性,其本人的小说也常带孩童视角,常有少年主题。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持久地遵循陀氏《双重人格》《罪与罚》《群魔》中的那种气质。因此,假若说《锦上》的创作手法受陀氏影响,这也不难理解。在这部小说里,他抛弃了全知全能的叙事套路,倾心于一个描摹的游戏。史诗作为“背景”或者“前景”,不是任意引用的,与受文形成对话结构或互补性指涉,既处理了“汉写民”文学如何还原和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问题,也整体拓展了小说外延性。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他仍一丝不苟地埋下铺垫,使得互文关系充满根据、有始有终。
就此而言,《锦上》的互文性反映在细节中,而互文性的意义就在于去衡量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创作效应。这也正是《锦上》的叙事意义,它制造了开放的阐释空间,读者在此获得充分的主动性。
(长篇小说《锦上》,甫跃辉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甫跃辉:实力作家、诗人,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五陵少年》《万重山》等。
本文作者高毅月:云南大理人,南昌大学研究生,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导师为著名小说家阿袁。)
高毅月
来源:青年报
- 相关推荐